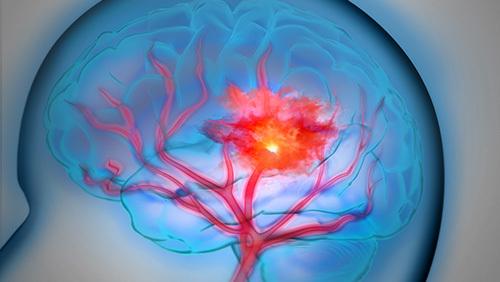重要特点
技术恐惧的重要特点是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心理与行为互动、内因与外源结合的结果,现实与文化并存,正负效应兼具,其实质是人与技术之间的一种负性关系。赵磊将技术恐惧界定为“主体的人和客体的技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引发的人对技术负面的心理与行为反应”,具体表现为人对技术的不适应,消极地接受技术或出现不同程度的抵制情绪,甚或对技术的否定与破坏。他还将技术恐惧归纳为:对新技术的本能排斥、拒绝与抵制;对新产品、新技术感到的压力、焦虑与恐慌等。韦尔(M. Weil)和罗森(L. D. Rosen)认为,技术恐惧是指人对计算机与相关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冲击与对未来世界可能产生的破坏等,由此衍生消极的、被动的甚至是抵触的情绪与看法。[1]
历史溯源
从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史来看,技术早期是作为人类祛除恐惧的手段而存在的。技术是人类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人们凭借技术去认识、改造自然。科学技术使人类可以解释自然之魅,可以祛除对自然界的恐惧。但为何技术会从消除恐惧的工具变为恐惧的对象?这与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以及技术本身属性有着直接关系。技术观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下形成的对技术的总体认知和把握,指导着人们对技术、技术行业及与技术有关活动的认知和态度。
技术恐惧分为古代技术恐惧与现代技术恐惧。古代技术恐惧主要是文化形态的技术恐惧,与古代的技术文化和人们的技术观密切相关。现代技术恐惧则是工具理性的技术认知与现代技术风险及风险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启蒙运动为科技发展开辟了道路,把科学技术理性从神学与宗教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又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提供了必要条件。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使技术不仅解放生产力、提高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成为人类统治自然界、破坏自然环境和资产阶级实现剥削的工具与帮凶。这样,科学技术就从人类的解放手段沦为统治枷锁,也因此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与环境危机。这也导致了以破坏机器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卢德运动,以保护环境、重返自然和拯救资本主义道德为主题的浪漫主义运动等,这些都是现代技术恐惧的萌芽和表现。[1]
形成机理
技术恐惧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技术本身不完善、经济利益的驱使、心理上的畏难情绪以及大众媒介的大肆渲染等方面。任何技术都有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周期过程,处于成熟前期的技术存在缺陷与不足在所难免,而且即使是成熟技术也会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关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特定行业的劳动者来说,技术进步将导致产业工人的减少,导致部分在岗人员失业进而产生对技术的抵触情绪。心理上的恐惧则是由某种场景或物体引起的消极、抵触的心理反应。一方面,表现在人对不可控之物产生本能、原始的敬畏与恐惧。另一方面,又表现在人对无法预料甚至关系生死存亡的敏感问题所生发的终极关怀与严重关切,以及恐惧特有的自我放大性与强烈的人际感染性而产生迅速、非理性的无限蔓延与扩散等,这与人对生的向往与死的恐惧密不可分。在大众媒介领域,大量悬疑与科幻作品渲染的生动形象的技术图景会使受众备感人类的渺小与卑微,也可能因此导致技术恐惧。
技术恐惧与其他恐惧形式存在一定差异,其并非仅源于人的心理问题,而且与技术的风险特征及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换言之,技术恐惧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形成的人与技术的某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一般通过负面情绪和消极态度表现出来,亦被称为负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恐惧”就是科鲁科达(A. R. Korukonda)所谓的“在一个组织语境中人与机器相互关系的结果”。区别于解决作为疾病的恐惧症需要着力于人的心理层面,解决技术恐惧问题需要从技术、人与社会三方面入手。当前,我们可以借助仪器对技术恐惧进行定性、定量的测量,可以通过获取的技术数据分析人们对某种技术产生的恐惧指标。可以说,技术恐惧是人对于同技术关系的一种本能反应,其程度通常受个人的技术观及对待技术的态度影响。[1]
应对之策
技术恐惧研究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与重要的现实价值。研究技术恐惧的目的是消弭恐惧,克服内心难以抑制的惧怕心理。消除恐惧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但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产生技术恐惧的主体——技术。我们可以变革技术的设计,让技术的设计者、开发技术软件的工程师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喜好、需求等生理与心理特点,进行更为人性化的设计,使生产的产品具有简单、方便、友好、宜人等特点,使其更易被人们所接受。二是技术恐惧的客体——人。我们可以改变使用技术的人,增加其实践机会,培养、提高其与技术相关的知识、技能,改变其消极、被动对待技术的态度,调适其心理以适应技术发展。
现代技术恐惧研究在关注技术恐惧对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不良影响的同时,更要关注如何正确应对技术恐惧,以消除或降低其消极影响并指出技术恐惧问题的解决进路。当我们面临复杂多变的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的技术风险时,除完善和变革现有技术、探寻新技术外,还要有对社会、对人类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仅关注技术的短期效益,忽略了长远利益,则有可能走向一种危险境地。因此,对于技术整体的发展路径,我们应立足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使其在规划、设计、生产、应用的所有环节都置于一种必要的制约与引导之中。
在约纳斯(Hans Jonas)看来,“道德行为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实践一种最高的善,而在于阻止一种最大的恶,并不在于实现人类的幸福、完美与正义,而在于保护、拯救面临着威胁的受害人”。质言之,道德的正确性正是对人类未来发展进行估量的基础上承担相应责任。人类面临的一切可能出现的风险与挑战,都需要尽可能地纳入相对完善的监测体系并进行有价值的预测与评估,以便我们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规避与防范。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消极、被动的研究,而要为预防风险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评估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的严重程度,从而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境地。这种研究因其对未来的预防性、预见性与前瞻性,便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我们需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全面的评估工作,完善必要的评价体系。
关于应对技术恐惧的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一是对片面追求技术的人的警醒作用,二是对技术发展道路的启示意义。我们应为人类未来谋福祉、以规避风险为导向,扩大责任担当与道德伦理的外延,找出一条更为符合时代发展的技术恐惧研究范式,以更好应对社会可能遭遇的风险与挑战。我们要在研究技术恐惧中形成一套应对恐惧技术的智慧,担负起责任与道义,对技术进行反思、理解与驾驭,将技术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我们需要在技术风险迭起的当代社会正确认识技术恐惧现象,学会在恐惧中前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