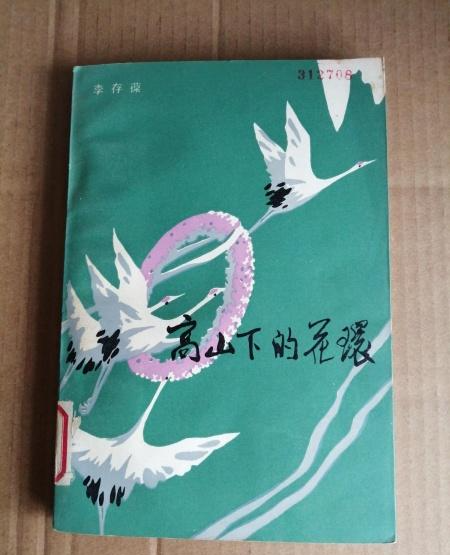内容简介
济南部队歌舞团的创作员李干事来到云南哀牢山中某步兵团三营营部,采访营指导员赵蒙生。赵蒙生出生于革命家庭,三年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荣立过一等功。三年多来,他毫不艳羡大城市的花红柳绿,默默地战斗在云南边陲,还动员他当军医的爱人也到边疆前哨任职。但是,他却多次拒绝接受采访,所以他的事迹一直未能见诸于报章。得知李干事是山东人而且三年前曾亲自到前线采访时,赵蒙生给他看了刚刚收到的退款单,和办公桌上方挂着的烈士梁三喜有照片。然后,赵蒙生给李干事提了三点要求:报道要写得朴实、真实,特别不能回避赵和他母亲不光彩的表现。李干事同意后,赵蒙生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1978年9月6日,原在军政治部宣传处当摄影干事的赵蒙生调到三营九连担任指导员。连长梁三喜热情地接待了他。梁三喜为人忠厚,生活勤俭,带兵极严,由于连队前任指导员上军校学习,他长时间不能回家探亲,所以很盼望赵蒙生的到来能为他分担一些担子。然而,赵蒙生到九连的真实目的却是搞“曲线调动”。他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父母都是部队高级干部。受十年动乱影响,他的母亲吴爽从一个无私的革命者变成了长袖善舞的“外交家”,赵蒙生也变成了养尊处优的“少爷”。就在吴爽利用关系要把儿子从边疆调回自己身边时,有“雷神爷”之称的雷军长重新回到军里任军长了。赵蒙生的母亲对雷军长有救命之恩,他本以为雷军长能同意自己调走。但没想到,雷军长到任后搞党委整风,抓机关整顿。在别人提示下,吴爽赶紧把儿子离开军机关,躲开“雷神爷”,然后再想办法调走。
一心要“曲线调动”的赵蒙生到九连后,魂不守舍,无心工作。对于这个生活懒散、军事技术水平稀松平常的指导员,以靳开来为首的基层官兵颇有微词,但是,梁三喜以大局为重,处处忍让体贴赵蒙生。赵蒙生却不领情,反而认为自己和这个“顶着高粱花子参军”的同龄人没有共同语言。由于赵蒙生这个指导员不合格,梁三喜不放心把连队交给他,决定再次推迟回家探亲的时间。
赵蒙生受不了基层连队的艰苦生活,催母亲早点把自己调走。吴爽来信中透露了赵所在的部队将有大行动的消息。十天后,赵蒙生的调令下来了,与此同时,部队也接到命令要上前线。赵蒙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向忠厚的梁进喜劈头盖脸地痛骂了赵蒙生。赵蒙生也知道在这种时候离开部队,是对军人称号的最大玷污。所以,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随部队坐上开往云南边防线的列车。到了前线后,梁三喜见赵没有离开连队,不仅没再向他投去鄙视的目光,反而像他刚下连时那样主动找他商量工作,还给靳开来等干部做工作,让他们不要歧视赵。然而,赵蒙生心里唯一的希望是离开战斗连队,回到军机关,在这一点上,他和母亲吴爽不谋而合。
在发起进攻前夕,吴爽把电话打到了雷军长的前沿指挥部,要求调走赵蒙生。雷军长大怒,在全体军人的面不点名地痛斥了这种可耻行径,赢得全体官兵的拥护。军长和官兵们的反应,让赵蒙生感到极大羞辱,也激发了他的自尊心和爱国心,他当着全连的面写了血书。
九连受命为尖刀连,具体任务是:在战幕拉开的当天,火速急插,务必于当天下午六时抵达敌364高地前沿,于次日攻占敌364高地,并死死扼守该高地。在战前支委会上,一向爱说牢骚话的靳开来主动要求担任带尖刀排。梁三喜也提出要带尖刀排,靳开来指出梁三喜家只有他一个儿子,而自己还有兄弟,所以他比梁三喜更适合。为了支援九连,军部把刚从北京调来的战斗骨干分配给他们。
九连在陌生的热带丛林中艰难行进。梁三喜发现新分配来的炮手智勇双全,便把他留在身边。这个战士让大家叫他“北京”。不了解战场实际情况的上级批评九连的行进速度慢,靳开来对这种瞎指挥非常不满,梁三喜命令大家轻装前进。在急行军中,司号员小金累死了。
为了赶路,大部分战士们扔掉了水壶和干粮,到达指定地点后,全连基本上粮尽水绝了。“北京”和梁三喜一起制定了进攻方案。战斗打响了,经过血战,九连占领了高地,打退了主峰敌人的三次进攻。但是由于缺水,战士们的战斗力明显下降。靳开来决定带人下山去砍越南人的甘蔗。虽然明知这是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靳开来宁愿被处分。没想到在半路上,他踩中了敌人地雷。临终前,靳开来唯一的心愿是再看一眼妻儿的照片。
主峰上有敌人的迫击炮阵地,一个劲地朝九连头上打炮,如果死守待援,九连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梁三喜果断决定,向主峰进攻,占领敌炮阵地。在战斗中,“北京”作战勇敢,却因为数发文革时制造的臭弹而失去战机,被敌人杀害。九连终于站在了364高地主峰上。就在大家欢庆胜利时,残敌打来冷枪,梁三喜为救赵蒙生而中弹,临终时,他右手紧紧攥着左胸上的口袋,有气无力地对赵蒙生说:“这里……有我……一张欠帐单……”在他上衣口袋里战友们找到一张染血的欠账单,上面记录了的每一笔借款,共计六百二十元。
战斗结束,整个部队班师回国,赵蒙生荣立一等功,但他心情却更加沉重,因为虽然梁三喜和“北京”评上了战斗英雄,而靳开来却由于违反纪律而不得评功。烈士们的家属陆续来到部队。赵蒙生把自己的一等军功章送给靳开来的妻子,谎称这是九连颁给靳开来的勋章。吴爽、梁三喜的母亲和妻子玉秀相继来到部队。吴爽、赵蒙生这时才惊讶地发现梁三喜的母亲便是曾在解放战争时帮助抚养过赵蒙生的梁大娘。而“北京”的父亲也来看望儿子的坟墓,他就是雷军长。
赵蒙生和战士们没有把梁三喜的欠账单交给梁大娘,本打算由连里出钱为连长还账,但梁大娘和玉秀临走前,根据三喜家信里的叮嘱,谢绝战士们的好意,拿出抚恤金和从家带来的钱,坚持把账还上。
故事讲完了,赵蒙生带领着九连全体同志和李干事,抬着一个个用鲜花编织成的花环,到烈士陵园,把花环敬献在烈士墓前。默立在百花吐芳的烈士墓前,李干事蓦然间觉得:人世间最瑰丽的宝石,最夺目的色彩,都在这巍巍青山下集中了。
创作背景
1979年春,李存葆以作家身份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后来,又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在那里,他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目睹了很多豪情悲壮的动人故事。在前线,李存葆边采访边写作,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发表在报刊上。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酝酿着一部刻画英雄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李存葆在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因此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账。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账可用抚恤金来还。这就是后来小说及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李存葆将早已构思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同《十月》编辑部编辑张守仁讲了,得到了张的支持。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回济南部队,而是在北京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安下身来,火速赶写,用半个多月就完成了全稿。
人物介绍
梁三喜
九连的连长,生于革命老区,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有着劳动人民本色且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解放军指挥员。和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他勤劳克己,敦厚善良,以“瘦骆驼”般的身躯承担着连队的工作和十年动乱中农村破产造成的经济压力。他为人笃诚,谦和、宽容,然而爱憎分明,决不饶恕临阵脱逃的懦夫。他忠于职守,把祖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献身。他牺牲时没有豪言壮语,只留下一张血染的欠账单,而且遗言中叮嘱让家人用抚恤金偿还上欠账。
靳开来
九连的炮排排长,自称“牢骚大王”。说话粗俗,爱发牢骚,而且每每切中要害,因此在领导眼中是个“鸡肋”。他有技术有能力,富有人情味,爱开玩笑,甚至有点玩世不恭,但在战场上,他深明大义,舍身报国,主动包揽了尖刀排的任务。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为了给饥渴的战友解渴,他冒险去砍了几捆越南人的甘蔗,不幸踩雷牺牲,结果死后受到不公正待遇,连一块勋章都没有。
赵蒙生
九连的指导员。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后代,出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解放初期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革命教育,但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父母的不幸遭遇,他的心灵受到创伤。父母复职后,他变得养尊处优,生活懒散,下连队也只是为了在母亲帮助下搞“曲线调动”,甚至在部队快上前线时想当“逃兵”。后来在正义力量的感召和血与火的考验中被唤醒了军人的爱国心和人格尊严,成为真正的战斗英雄。
薛凯华
从北京调到九连参加战斗的战士,自称“小北京”。其实是雷军长的儿子,随母亲的姓。他从不以将门之子自矜,胸怀大志,才华过人,生气勃勃,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在战场上表现英勇机智,深得梁三喜信任,却因几颗文革期间生产的“臭弹”而牺牲。
梁大娘
梁三喜的母亲,赵蒙的养母。一生历尽千难万苦,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她生育的三个儿子,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二儿子为他人牺牲,梁三喜是她最后一个儿子,然而也倒在了保卫祖国的战场上。她善良、无私、刚强,没有向国家提任何要求,更婉拒三喜战友们的资助,坚持按三喜的遗嘱,用烈士抚恤金和家里凑的钱还清了他的欠账。
吴爽
某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贫苦出身,战争时期为革命出生入死,曾救过雷军长的性命。经过十年动乱后,她以功臣自居,忘掉自己革命的初衷,心安理得地走后门拉关系,变成了“外交家”,想方设法把子女调到舒适的岗位,甚至在开战前夕把电话打到前线指挥部,要求把自己的儿子调离战场。
雷军长
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被称为“雷神爷”,在军中享有极高场望,治军极严,令行禁止。解放前,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出生入死,解放后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疾恶如仇,不怕丢官坐牢,是铁打的硬汉。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建国后十七年的一些军事小说往往忽略了军队生活与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视野狭窄,近乎成了一种孤立的“军营文学”。而《高山下的花环》作品将带有各种社会因素的人集中于战场,将军营与社会、军队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广泛联系起来。赵蒙生为求安逸而“曲线调动”,下到连队,敷衍待命,其战前的心灵和表现与复杂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梁三喜浸血的欠账单连接了老区人民的生活,浓缩了时代的特征。赵蒙生与梁三喜两家的悲欢离合,昭示了老区人民与军队的血肉联系。
小说大胆地揭示了军内矛盾和社会矛盾,展现出深广的社会内涵。部队参战在即,指导员却魂不守舍,一心搞“曲线调动”;大战前夜,高干夫人打电话到前沿指挥所为儿子开后门;靳开来为国捐躯,却没有军功章;梁三喜所留的“遗书”是带血的欠账单;薜凯华死于生产于文革时期的臭弹等等,深刻地展现社会“极左”思潮造成的恶果。在揭露不正之风的同时,作者通过描写那些军队生活中的矛盾透视出军人的苦乐观、是非观,展现了中国军人具有的“位卑未敢忘国忧”的坚韧顽强、英勇崇高的内在力量,歌颂了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
艺术特点形象塑造
小说塑造人物时,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从社会实际生活出发,从人物的个性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从模式出发,对丑的不粉饰,对美的不夸大,更不神化。靳开来说话粗俗,但他说着怪话,做的却是好事;指导员赵蒙生既有自私、庸俗的一面,又不乏人格自尊。这样的手法深刻揭示了作为普通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成长和转变。
同时,作者注意描写一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的互相冲突。赵搞“曲线调动”下连队当指导员,他生活懒散,业务水平稀松,还瞧不起农村出身的连队干部,在馒头事件、休假问题上与梁三喜起冲突。对此,治军甚严的连长梁三喜再三忍让,但当部队即将上前线,赵蒙生却在母亲帮助下搞到了调令时,忠厚人梁三喜一下变成靳开来,怒斥这种逃跑行为,尚知军人报国当义无反顾的赵蒙生含羞登上南下军车,此时梁三喜又异常高兴,大小事情都同赵商量,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在一系列冲突中,展现了梁三喜谦和忍让又爱憎分明的性格,也为赵蒙生日后心灵的净化埋下伏笔。在特定的环境中,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互相撞击,使各自迸发出思想火花,并以此揭示生活的矛盾和人生的意义。
以情动人
作者一改之前军事作品“神化”、“净化”英雄的倾向,通过真实的描写,将英雄豪情与人之常情统一起来。在临上前线时,连从来都抽劣等旱烟末的梁三喜竟也破例买了两盒“红塔山”,因为在告别人生前最后体味一下生活赐与人的芳香,乃是人之常情。小说中英雄靳开来在激烈的战斗中随身带着全家的合影,并且记得儿子的生日,牺牲前他也没有豪言壮语,而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对妻子、孩子、母亲的挚爱。而他死后不能评功的结局,也让作品充满了悲剧色彩。
结构特点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给人自然亲切真实之感。小说的第一人称并非一成不变,开头的“我”是采访战斗英雄赵蒙生的记者,而小说的主要情节以“我”(赵蒙生)为故事叙述人,同时在故事叙述过程中第一人称随情节需要转换。作品从“我”思想发展过程的层次更迭和“我”所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来构成艺术画面,形成波澜。正是由于采用第一人称口述的形式,小说的语言显得自然质朴亲切,节奏流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但是,小说的结尾比较粗糙,几封遗书接连出现及两封家书的出现(赵母和梁母都来了信,而且都送给记者看了)很仓促,而且两封家书写得过细过长过于质直,就艺术性而言尚有不足。
作品影响
《高山下的花环》在20世纪80年代开创了以悲剧形式反映战争和军营生活的创作先例,是军旅小说的一个决定性突破。从此以后,军旅小说的创作在题材领域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所涉及的题材几乎贯穿了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再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各个历史时期。
该小说在《十月》发表后,中央及各省市报纸争相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先后有74家报纸全文连载,50多家剧团改编上演,曾创下单行本180万册的印刷量。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曾自费购买了两千册赠送给南疆战士。该小说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入选1989年美国嘉兰德公司出版的“20世纪世界文学丛书”。
1983年,山东电视台将小说改编成三集电视剧,由周里京主演。1984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故事片上映,该片由谢晋导演,吕晓禾、唐国强等主演。
2018年9月27日,《高山下的花环》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作品评价
陈思和:小说结构大开大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的演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品格调雄浑悲壮,具有一种英雄悲剧特有的冲击力……虽然在艺术上尚有粗疏之处,人物关系的设计也有过于戏剧化的痕迹,但其拥有的现实主义力量,使它为“文革”后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冯牧(《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好作品,一部充溢着崇高的革命情愫、能够提高和净化人们思想境界的作品。
作者简介
李存葆(1946—),作家、诗人。山东五莲人。曾用笔名茅山。初中毕业回乡务农两年后,于1964年参军,曾任排长,后调团政治处任新闻干事。1970年调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创作室任编导。1979年春,赴云南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采访,荣立三等功。1984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6年起任济南军区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1997年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舞剧《火中凤凰》、报告文学《将门虎子》、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报告文学《沂蒙九章》、散文《我为捕虎者说》等。

李存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