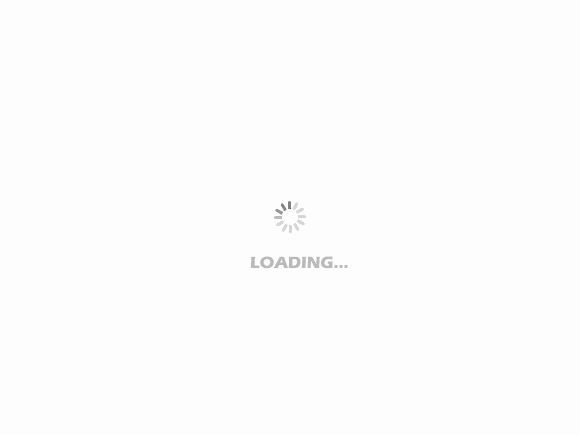时代社会背景
小说从1805年写起,一直写到1821年十二月党人酝酿起义。这部小说的主要历史背景是1812年法国入侵俄罗斯,这是拿破仑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俄罗斯爱国主义高涨的时期。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十二月运动与此事件密切相关。1825年,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起义被镇压。1856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呼声下被迫废除了农奴制,并赦免被判流放的十二月党人。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托尔斯泰。他决定为自己所尊敬的十二月党人写一部小说。但随着思考的深入,原定的构思不断被修正。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让人们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产生了新的认识,因而对1812年俄法战争的记忆也出现了争执。对保守派来说,1812年战争是俄罗斯贵族的功劳。但托尔斯泰作为民主派,受到俄罗斯农民战士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做牺牲的鼓舞,将1812年战争也视为是人民的胜利,认为此战依靠了整个国家的爱国精神。《战争与和平》显然贯穿了托尔斯泰“人民史观”的影响。普通士兵和农民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得到凸显,而上流社会特别某些贵族在战争面前的苟且偷安则成为被谴责的对象。 作者创作背景
托尔斯泰一生经历丰富,见证了俄罗斯民族转型时期的动荡与苦难。《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5到1869年,创作过程复杂曲折且耗时长久。在创作期间,托尔斯泰不仅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还亲自去战争现场考察,力图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场景。《战争与和平》最早于1865年开始在《俄罗斯通报》上发表,1869年完成第六册后,托尔斯泰又继续往前追溯。这本意在描述十二月党人的小说,背景原本设置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之后,但托尔斯泰对十二月党人的研究越多,就越认为他们的理论根源,实际上来自1812年俄法战争,于是托尔斯泰修改了《战争与和平》故事的发生时间。以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十九世纪60、70年代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具有独特史诗性。可以说,《战争与和平》最大的艺术魅力便在于对整个历史时代的记录与复活,对于民族意志与国家战争的追怀。 内容情节
第一卷
故事开始于1805年7月,安娜在彼得堡举办了盛大舞会。彼埃尔和安德烈都参加了这次舞会,并就俄罗斯与拿破仑法国的迫在眉睫的战争进行了辩论。当时法国军队入侵奥地利,作为奥地利盟友,俄罗斯派军队帮助奥地利,法俄关系紧张。安德烈告诉彼埃尔自己就要上前线去了,彼埃尔则表示自己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不会参战。彼埃尔后来从彼得堡回到莫斯科,继承了父亲基里尔·别祖霍夫伯爵的巨额遗产。安德烈则将妻子丽莎送往父亲领地后便去军队了。10月,安德烈在奥地利担任俄奥联军总司令库图佐夫的副官,而尼古拉·罗斯托夫则驻扎在胡萨尔团。面对战场上的混乱和上级的冷漠,安德烈和尼古拉都对战争的刺激和荣誉感到有些失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安德烈所在的俄奥联军在和拿破仑军队的大战中惨败。安德烈也受了重伤,思想发生剧烈变化,不再执着“荣誉”,觉得一切都是幻觉和虚无。 第二卷
瓦西里贪图钱财,因而说服彼埃尔娶了自己的女儿埃伦。埃伦生性放荡,婚内多次出轨,彼埃尔曾为她和自己的朋友、军官多洛霍夫决斗,彼埃尔在决斗中出人意料地胜利了。埃伦指责彼埃尔不该去决斗,彼埃尓愤而与埃伦分居,独自一人去了彼得堡。在前往彼得堡的路上,彼埃尔偶然加入共济会。埃伦则在彼埃尔外出期间,爱上了安娜的儿子鲍里斯。在共济会宽容博爱精神的指引下,彼埃尔原谅了埃伦的又一次出轨。彼埃尔开始将自己的精力放在自己庄园的农奴制改革上,试图通过解放农民来实现新信仰,但他手下的总管们总是阳奉阴违,农奴们依然如故。与此同时,被军方误报死亡的安德烈回到家中,得知妻子丽莎在分娩时去世。彼埃尔去看望了伤愈后回来的安德烈,想向他宣传共济会教义,但战争创伤和妻子去世使安德烈感到深深的幻灭感,他决心只为自己而活。 1807年6月,弗里德兰会战,俄国胜利,俄法签署了和平条约。尼古拉目睹了野战医院的可怕条件,士兵的痛苦和俄帝国的浮夸作派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感到无比失望。1809年,安德烈参观了罗斯托夫家的乡间庄园,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尼古拉的妹妹娜塔莎,对她一见钟情,找到了人生的新希望。安德烈搬到彼得堡并担任政府职位,罗斯托夫一家也搬到了彼得堡。安德烈没多久便向娜塔莎求婚了,但由于安德烈父亲的干预,安德烈和娜塔莎被要求等待一年再结婚,安德烈被父亲送往国外。与此同时,彼埃尔愈来愈发觉共济会的虚伪,开始重新致力于自己的婚姻。尼古拉则不情愿地离开了军队,回家帮助解决父亲混乱的财务状况。在此期间,尼古拉和表妹索尼娅旧情复燃,但由于尼古拉母亲的反对,两人未能结合。娜塔莎则在莫斯科遇到了阿纳托利·库拉金,两人产生恋情并计划私奔。但阿纳托利实则是有妇之夫,他只是计谋将娜塔莎拐卖到国外。阿纳托利的诡计终以失败告终,阿纳托利被赶走,娜塔莎因羞愤和懊悔多次试图自杀。彼埃尔来安慰伤心的娜塔莎并袒露自己爱她。安德烈回来后发现了娜塔莎的不忠,两人解除了婚约。 第三卷
1812年6月,拿破仑的军队入侵俄罗斯。安德烈重新参军,起初,他希望找到与阿纳托利决斗的借口,但很快,军队紧张的生活节奏使他淡忘了这一想法。安德烈因表现英勇被任命为轻骑兵指挥官。与此同时,无所事事地生活在莫斯科的彼埃尔渴望为战争作贡献,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援,他开始痴迷于刺杀拿破仑的想法。
1812年8月26日,波洛金战爆发,莫斯科情况危急。彼埃尔突然离开莫斯科前往博罗季诺的前线。在博罗季诺战役的前一天晚上,彼埃尔和安德烈最后一次交谈。第二天,彼埃尔观察了雷夫斯基堡垒的残酷战斗。安德烈则被一枚爆炸的炮弹严重打伤。战斗的结果很模糊,两支军队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库图佐夫坚称俄罗斯已经获胜,但法国仍有足够的动力向莫斯科推进,迫使俄罗斯撤退。法国军队逼进的消息使安德烈的父亲受刺激过度而死。安德烈的妹妹玛丽亚准备逃跑,但叛变的农民干扰了玛丽亚的疏散。尼古拉赶来救玛丽亚,在此期间,两人互生好感,玛丽亚坚韧的性格深深吸引了尼古拉,两人因而产生了一段恋情。莫斯科渐渐陷入了混乱,受伤的军人被带走,市民乘坐满载的手推车逃离城市。当罗斯托夫一家撤离时,许多士兵在他们的大篷车里搭便车。娜塔莎不知道,安德烈也在其中。 9月2日,莫斯科发生不明大火。从博罗季诺回来的彼埃尔仍然确信杀死拿破仑是他的使命,继续留在莫斯科试图杀死拿破仑。然而,当莫斯科被烧毁时,他因保护一名妇女免受法军侵害而被法军当作纵火犯抓捕。与此同时,娜塔莎发现了伤员中的安德烈。半夜,她偷偷溜到安德烈的床边,两人泪流满面地团聚了。出于内心的愧疚,娜塔莎悉心地照料重伤的安德烈。9月30日,拿破仑进入莫斯科。此时的莫斯科已几乎是空城。
第四卷
由于缺乏补给,法军未能在莫斯科久留,彼埃尔也被一并带走。在被俘期间,彼埃尔认识了农民卡塔拉耶夫,他的智慧激发了彼埃尔的生存意志。受到卡塔拉耶夫思想的启发,彼埃尔试图奉行“勿以暴力抗恶”“听天由命”的哲学去生活。埃伦则得了一种“人们津津乐道的可怕疾病”,她大量饮下某种只能小剂量服用的药物,随后死去。她死后,她的父亲找开药的医生问罪,医生拿出一沓她生前写的信,她父亲便立刻不追究了。玛丽亚得知安德烈的下落后赶往罗斯托夫家。娜塔莎日以继夜地照顾安德烈,安德烈不再害怕死亡,在原谅了娜塔莎后,他度过了最后的日子,沉思着永恒的爱。安德烈终因伤势过重去世。
俄国饥寒的冬天冻死了大量法军,战局得到扭转。塔鲁蒂诺战役后,法国军队开始恐慌和撤退。彼埃尔在监狱和游行中找到了和平与满足。娜塔莎的弟弟佩蒂亚·罗斯托夫在一场战斗中被枪杀,在照顾悲伤的母亲的过程中,自安德烈去世以来一直沮丧的娜塔莎找到了新的生命。俄军乘胜追赶战败的法国人,许多俄国士兵和彼埃尔一起被释放。彼埃尔于1813年1月回到莫斯科,当他向成熟后的娜塔莎倾诉自己的经历时,她以敏感和同情心回应,他们逐渐互相爱慕。后来在玛丽亚的帮助下,彼埃尔和娜塔莎结合。尼古拉父亲去世后,尼古拉搬回莫斯科,偿还他父亲的巨额债务。1814年,尼古拉与玛丽亚结婚,安德烈的孤儿则与他们一起生活。 人物形象
家族及成员
家族 | 主要成员 |
别祖霍夫家族 | 1.彼得·基里尔洛维奇·别祖霍夫(彼埃尔,基里尔·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后立为子嗣,继承了他的遗产。) 2.基里尔·别祖霍夫伯爵 |
鲍尔康斯基家族 | 1.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 2.伊丽莎白·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丽莎,安德烈的妻子) 3.尼古拉·鲍尔康斯基公爵(安德烈的父亲) 4.玛丽亚·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安德烈的妹妹) |
库拉金家族 | 1.瓦西里·库拉金公爵 2.埃伦·库拉金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的女儿) 3.阿纳托列·库拉金公爵(瓦西里公爵的儿子) |
罗斯托夫家族 | 1.娜塔莉娅·罗斯托娃伯爵小姐(娜塔莎) 2.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娜塔莎的父亲) 3.娜塔利娅·罗斯托娃伯爵夫人(娜塔莎的母亲) 4.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娜塔莎的哥哥) 5.佩蒂亚·罗斯托夫伯爵(娜塔莎的弟弟) 6.索尼娅(娜塔莎母亲的外甥女) |
德鲁别茨科伊家 | 1.安娜·米哈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 2.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安娜的儿子) |
其他 | 亚历山大一世(俄国沙皇)、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皇帝)、库图佐夫(俄军总司令)、巴格拉季昂公爵(俄国野战军司令)、涅斯维茨基公爵(传令官)、季莫欣上尉(军官)、丘申(炮兵军官)、杰尼索夫(军官,尼古拉的朋友)、多洛霍夫(谢苗诺夫联队的降级军官) |
资料来源:
主要人物简介
人物 | 简介 |
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 | 冷静理智,善良正直,同情底层人民,对所处贵族阶级的虚伪堕落深感不满。为探索生命意义与国家前途积极投入战争,前期渴望建功立业,后来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荒诞后,思想上发生巨大变化,渴求亲近自然、向往日常生活与人间之爱。 |
彼得·基里尔洛维奇·别祖霍夫(彼埃尔) | 感情冲动,缺乏意志力,但淳朴善良,执着追求道德理想。欣赏拿破仑和共和国体制。因与埃伦的不幸婚姻备受精神折磨,后加入共济会渴求解脱。在认识到其虚伪性后转而将生命热情转移到对娜塔莎的爱中。卫国战争发生后,与人民的接触和成为战士的信念赋予了其真正的新的生命,使其投身到反抗农奴制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中去。 |
尼古拉·罗斯托夫 | 娜塔莎的哥哥。性格冲动,渴望参军。与索尼娅是初恋情人,因拒绝家族安排的婚姻而入伍,最终与与玛丽亚结婚。 |
娜塔莉娅·罗斯托娃伯爵小姐(娜塔莎) | 前期性格纯真浪漫,富有灵气。后期经过战争和婚恋的洗礼逐渐变得坚韧顽强、有责任感。在战争中悉心照顾伤员和残疾的安德烈。初恋是鲍里斯,后经过一场舞会的邂逅,与安德烈订立婚约。在被阿纳托利吸引后,解除了与安德烈的婚约。最终与彼埃尔结合。 |
玛丽亚·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 | 安德烈的妹妹,至善至美的代表。因相貌平平而迟迟未嫁,性格温顺善良、宽容博爱,最终与尼古拉结婚。 |
埃伦·库拉金 | 美丽而放荡,道德堕落、内心空虚。因慕财与彼埃尔结婚,在婚内多次出轨,最终两人离异。 |
伊丽莎白·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丽莎) | 安德烈的妻子,性格活泼,单纯可爱,善于交际。在乡下待产时因想念城里的生活而时时苦闷抑郁,最终难产而死。 |
索尼娅 | 娜塔莎母亲的外甥女,以孤儿身份寄居在罗斯托夫家。善良真诚,深爱尼古拉,和他是青梅竹马,也是初恋情人。但为家族利益和爱人幸福甘愿牺牲自己。 |
主题思想
人道主义与博爱思想
《战争与和平》不仅有对人道、博爱思想的直接表述,诸如“不要用暴力和邪恶抗争”“道德上自我改善”等。还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安排进行间接呈现,从具体的人看,即使如海伦(埃伦)这样堕落的灵魂,亦被给予了反省和自我救赎的机会,这是宽恕、博爱的精神体现。从阶级来看,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贫民悲惨命运的专注与描写以及同情的表达,亦凸显了人道主义精神。《战争与和平》寄寓了托尔斯泰希望人类通过战争和苦难向和平与安宁的农耕社会回归的理想,希望实现人类生命的终极超越与举世的和谐融一。这实际受到了卢梭思想的影响,希望建立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乌托邦。由于这样的理想几无实现的可能,博爱思想便成为一种现实的替代,《战争与和平》即内涵着以博爱来改变社会,克服罪恶;以爱的力量感召人弃恶从善,甚而放弃战争的思想。这样的道德思想也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这一思想被鲁迅理解为“不抵抗主义”予以批判。 命运与人生
在《战争与和平》中,人物被置于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之中,呈现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无常命运与与人生抉择之间的深刻悖论。面对时代的沧桑巨变,在生命的抉择过程中,每个人都经历了曲折复杂的精神蜕变,哀乐交织,百感交集。实际上,在《战争与和平》中始终萦绕着一股神秘的力量,这种近乎宿命和“天道”的东西,托尔斯泰称之为“最高法则”和“命运规律”,认为是命运在冥冥中左右了历史的整体走向与个体的人生,人们只是被动服从。因而《战争与和平》中出现了如安德烈、彼埃尔一类,以理性审视自身存在而陷入了绝望和怀疑深渊之中的人物,小说的最后也走向了某种非理性的神秘主义。
民族性与阶级性
《战争与和平》为了批判西方道德观,有将民族性神化的倾向。卡拉塔耶夫的农民肖像即是小说中最为突出的民间形象,作为一种民族性叙事意识形态的核心,启发了彼埃尔这个失落贵族,使其找到了真正的人生道路。这一民间形象作为一种象征,建构了一种浪漫的神话性整体,以挑战包括作者自我在内的西方理性智力环境。这种对农民理性化的描绘近似亲斯拉夫派的世界观,特点是保守和崇尚乌托邦。《战争与和平》中的威胁主要来自外族入侵,内涵对传统“超稳定结构”的维护,否定激进革命,颂扬传统家庭制度,从家庭的神圣性进而延伸到阶级制度的神圣性。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倾向。小说中人物的阶级背景被强化,拿破仑被暗讽为一种“暴发户”。其入侵的失败在小说中象征着传统“和谐”状态的恢复。此外,安德烈庄园的农民起义被描述得毫无意义,甚至被视为毫无道理的混乱,也显示了小说的保守立场。
爱国主义
《战争与和平》还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实际也是民族性的一种体现。通过对社会各个阶层典型代表的概括描绘,大体勾勒不同阶级在国家兴亡面前的态度,表露了作者的立场与爱憎。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赞扬庄园贵族、普通民众及士兵的爱国精神,歌颂他们善良正直与勇敢奉献的品质。对于虚伪自私的宫廷贵族、达官显贵,则给予揭露、嘲讽与批判。实际上,爱国主义可以看做是《战争与和平》的主旋律,除了对俄国社会各阶层的褒贬分析,对敌我双方“两套笔墨”的描写也是典型体现。对拿破仑军队漫画式的嘲讽批判态度与对俄方军队的热情歌颂形成了鲜明对比。
艺术特色
史诗性
托尔斯泰自己就曾在创作日记中表示,《战争与和平》要以《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为范本,描绘一幅“置基于历史事件之上的风俗画”。《战争与和平》的确融合了《奥德赛》的日常生活与《伊利亚特》宏伟战争场面,建构了一幅俄国近代生活全景图。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高度融合,细节与整体、个人与群像相互映照的完整结构奠定了小说的史诗性基调。 从宏观来看,《战争与和平》不仅细致真实地描绘了数量众多的战争场面,而且展现了近代俄国辽阔的地理环境和复杂丰富的人情风貌。从城市到乡村,从宫廷到农田瓦舍,俄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其中众多不同阶层、身份的人物典型都得到以点带面地呈现。
从微观来看,《战争与和平》实现了广度和深度的结合。在刻画巨幅群像和宏伟战争的同时,又能凸显日常生活和个人面貌,并且能够深入人物内心,在宏大叙事中穿插个人独白。此外,小说格外关注个体在国家、民族命运整体走向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讴歌了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时空叙事
《战争与和平》实现了微观个体与宏观历史的高度统一,特别是利用特殊的时空叙事,立体地展现了时代与人物特点。
在时间叙事方面,文本的叙事节奏与时序建构出了回环往复的韵律性的叙事时间,呈现出时间的立体构造。或逆转时序,或悬置时间,使多重线索得以结合,构造出完整的故事。小说无通常意义上的开端和结尾,而是聚焦主人公精神活动,把他们拖入了连续永恒的生命之流中,通过巧妙的宏观布局,实现了个体命运和宏大叙事的双向互动。安德烈、彼埃尔、娜塔莎等人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同时,历史又在不知不觉间改变和左右着他们的命运。
在空间叙事方面,通过心理和物理的内外双重空间构造,建构起文本框架。首先,不同的物理空间被赋予了各自的独特的内涵,在宫廷与瓦舍、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以典型环境的塑造来烘托人物形象和内心活动。其次,对于人物心理空间的细致挖掘,窥探到了隐没在宏大叙事下的隐秘心灵世界,特别是对于安德烈反战厌战情绪的刻画,使内外两个世界得以相互参照对比,更好地揭示出了历史的真与伪,突出了反战的主题。
女性形象
《战争与和平》中诸多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及她们的命运与结局,显露出特定的女性观,即理想的女性应该努力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拥有坚韧勇敢的品质,自尊自爱,富有奉献精神。女性的内在美高于外在美等等。此外,《战争与和平》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一种差序等级体系,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的臧否褒贬。以娜塔莎为典范和核心,依据与她关系的远近亲疏,呈现为一个“女性谱系”。以娜塔莎为代表的女性被肯定,以玛丽亚为代表的女性则属于可改造的,而以埃伦为代表的女性则是被否定的。 心灵辩证法
托尔斯泰善于从动态角度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的实际运动过程。这种手法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心灵辩证法”。在《战争与和平》中,这种手法突出表现在安德烈和彼埃尔两人身上。安德烈被战争的残酷与荒诞所深深触动,从一开始内心充满保家卫国的勇敢热情,逐渐陷入到无意义的迷茫与困顿之中。而彼埃尔深陷不幸的婚姻,倍受精神折磨,一度向宗教寻求解脱。此外,战争背景的设置,使《战争与和平》充斥着大量的死亡,几乎三分之一的人物在故事中死去,由死亡和生活无意义的结合引起的存在主义式焦虑逼迫人们审视自己的内心,直视生活和生命的真相。死亡成为人们审视内心和发生转变的催化剂。《战争与和平》正是通过曝露人类对自己心灵的自我观察,展现了人类复杂而矛盾心理世界。再加上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复杂多样环境氛围的烘托,使人物心灵和性格变化历程得到明晰和丰富的展现。
“作者小说”
在《战争与和平》的文本中,不仅穿插着作者托尔斯泰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诸多议论和独特人生观念的表达,还有数量不少的专章历史论述,在小说结尾甚至附有长篇论文。这在小说艺术领域,属于托尔斯泰独特的创造,使作品烙印上作者个人的鲜明印记。但这与托尔斯泰自己在《艺术观》中树立的艺术原则相违背,构成了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之间的一种悖论。小说成为了表达托尔斯泰个人理性意志和独特历史观的一种形式载体。
作品影响
社会影响
《战争与和平》作为一部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巨著,一方面,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看法,具有历史和社会学价值。屠格涅夫认为《战争与和平》提供了关于俄罗斯真实而直观的知识,写出了俄国人民的气质和性格,克鲁鲍特金认为《战争与和平》揭露了真实的历史和俄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王尔德也认为《战争与和平》不仅生动地写出了各色的人物,写出了他们复杂的思想与情感,还如实地反映了俄罗斯家庭的方方面面,透过人物描画出了整个时代的风貌,展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真相,讽刺力度十足。屠格涅夫也认为,《战争与和平》更加直接和准确地反映了俄国人民的精神气质和俄国生活,甚至胜过民族志和地理志。 文学影响
就托尔斯泰的个人创作历程而言,《战争与和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其创作和思想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战争与和平》更是影响深远。屠格涅夫、列宁、高尔基都认为它是十九世纪文学的第一流作品。作为托尔斯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以往创作的集大成者,《战争与和平》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欧洲影响的小说,它综合性地继承了欧洲小说的丰厚传统,将长篇小说的艺术体裁发展到了极致,构成了俄国小说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崛起的标杆。《战争与和平》奠定了托尔斯泰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地位,使之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继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之后的又一高峰。《战争与和平》亦常常被认为人们尊为“最伟大的小说”。
作品评价
俄国文学批评家斯特拉霍夫高度赞扬《战争与和平》对于人物心灵的细致描绘,肯定它是“现代艺术形式的一部史诗”。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当时最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赞颂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评价其写出了生与死的纠缠、幻灭与谎骗,自然的无形与神秘与无穷的博大与眩惑。
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则一方面高度评价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对灵魂的深度挖掘,扩展了人的内心世界。但另一方面则认为作品呈现出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认为托尔斯泰在作品中谴责沙皇、教会、国家,诅咒战争、嘲笑革命,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恐怖深渊,呈现出了民族巨大转型时期的苦难和阵痛,但却又不能扭转世道,他所信仰的精神是与现实情况相抵触的过眼云烟。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编辑Michael Dirda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一个关于矛盾的人类心灵的深刻感人的故事。
英国作家王尔德认为《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最负盛名的小说,小说长度与其复杂的情节和众多的人物数量相匹配。小说在情节建构上的散漫,是托尔斯泰创作天才的表现。
英国作家毛姆:虽然《战争与和平》有不少地方写得过于沉闷,读起来令人乏味。但仍然无法否认其伟大性。它以史诗般的大手笔描绘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和发展。它写出了人生的纷扰,以及在与决定各国命运的黑暗力量的对照下,个人的卑微和渺小,给人一种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译本信息
版本类型 | 翻译年份 | 相关信息 |
法文版 | 1885年 | 首部法文版,由阿谢特书店发行,共三册。 |
英译本 | 1886年 | 首部英译本,由Clara Bell翻译。 |
1889年 | 由 Nathan Haskell Dole翻译。 |
1904年 | 由 Leo Wiener翻译。 |
1904年 | 由Constance Garnett翻译。 |
1923年 | 由 Aylmer 和Louise Maude翻译。 |
1957年 | 由 Rosemary Edmonds翻译。 |
1966年 | 由 George Gibian翻译。 |
1968年 | 由Ann Dunnigan翻译。 |
2005年 | 由Anthony Briggs翻译。 |
2007年 | 由Richard Pevear 和 Larissa Volokhonsky翻译。 |
2010年 | 由 Amy Mandelker翻译。 |
中译本 | 1931~1933年 | 《战争与和平》(第一册),郭沫若译,上海文艺书局出版。 |
1947年 | 郭沫若、高植译,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
1949年 | 董秋斯译,上海书报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人大出版社出版。 |
1957年 | 高植译,新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出版。 |
1981年 | 黄文范译,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 |
1985年 | 纪彩让译,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 |
1988年 | 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1992年 | 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
1995年 | 盛震江、廖纲源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 |
1999年 | 周煜山译,天津人民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
2003年 | 张捷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
2010年 | 娄自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
衍生作品
1966年苏联版电影《战争与和平》长达六个半小时,耗时五年拍摄,并由苏联军方协助,是影史上动用临时演员最多的影片之一。此片耗资五亿六千万美元,堪称影史上最昂贵的影片,在苏联和世界电影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获得第4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宏伟巨制,以宏大场面和史诗般的镜头语言,忠实地再现了托尔斯泰原著的庄严雄伟,呈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俄国社会广阔的历史画卷。 1972年,英国BBC发行电视剧版《战争与和平》。
2001年2月,莫斯科福缅科工作室剧院上演《战争与和平·开端》(Война и мир. Начало романа)。作品准备长达7年,最终只将小说的开篇章节搬上舞台。
2015年12月24日,俄国圣彼得堡大剧院上演舞台剧《战争与和平》。
2016年,英国BBC发布新版电视剧《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