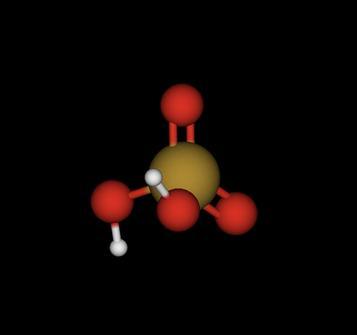产生背景
世界中心的不断转移,是地缘政治的权力转移,由地缘政治所决定。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导致了财富的革命,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必须为经济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最早期的南方丝绸之路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所探索和开辟。
名称由来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四川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四川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
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四川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丝路历史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南方丝绸之路路线图
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1]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当时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可能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1]
《史记》记载了中、印、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也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

南方丝绸之路
早在张骞尚未打开通往西域,开辟北方丝绸之路以前,西南先民们就已打通了一条从四川成都至云南滇东一带的“五尺道”,《史记》载:“秦时常頞通五尺道”,“五尺道”从四川出发往东南行,经僰道(宜宾)、南广(盐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继续向西至叶榆(大理)。《司马相如列传》载:“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武帝派遣司马相如积极开凿通川南雅安、西昌及云南大姚之邛、笮、井、駹等西夷地区的“西夷道”,因此道通过了越西境内的“灵关”,故又名“灵关道”,从蜀地南出,经临邛(邛崃)、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邛都(西昌)、会无(会理)、渡过金沙江到青蛉(大姚),抵达叶榆。在打通了身毒道之后,连接滇、川的通道蜀身毒道即可畅通而行了。以上两条在大理汇合后西行,经博南(永平)、永昌(保山),由越赕(腾冲)出境入骠国(缅甸),称为“永昌道”。此道在中国境内约有3000多公里。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中国较早的对外陆路交通线,同时也是中国西南与西欧、非洲、南亚诸国交通线中最短的一条线路。唐宋时期茶马贸易兴起,成为南方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交易商品,并且绵延千年而不衰,影响深远,因此又被后世称为茶马古道。明清茶马互市是南方丝路发展的鼎盛时期,分别从不同口岸与缅甸、印度、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发生着日益密切的往来关系,尤其将滇茶、川茶运进吐蕃,又将战马源源不断供应给中原。互相之间物资交流频繁,而且通过古道将文化进行了串联,以商品将文化形态碎片式的呈现,圈内圈外文化被勾连,因此南方丝绸之路从出现以来一直存在着多种文化的碰撞、传播、涵化、变迁,由于西南深处两端不同文化类型的中间地带,文化在此碰撞不仅异常激烈,而且包容和谐,时至今日呈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从边城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物资战略要冲,每天从烽火线上抢运着供往内地稀缺的生活物资、武器弹药、医疗设备,此时的南方丝绸之路是自开通以来最为繁盛的阶段,自身作用也发挥到了极致,为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结束之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恢复通车,之后随着现代化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南方丝绸之路被214、317、318国道、铁路甚至航线所代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南方丝绸之路逐渐沉寂。然而,作为历史的见证,南方丝绸之路成为文化遗传密码融入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构建起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蜀身毒道
《史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欲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张骞于建元二年行至陇西,经过匈奴控制区域,被俘,十三年后,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历尽艰辛辗转回到长安,虽没有达到出使大月支联合抗击匈奴的目的,但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成功的。张骞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 ,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据大夏人告之购自身毒(今印度),张骞推测在大汉的西南方有一条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国转而至大夏。《后汉书》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在此以前,汉代还完全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这就是蜀身毒道。而此时此道还不是官道,仅为民间商道。汉武帝意欲通过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期彻底孤立匈奴,便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几次派人到滇国,希冀打通通往大夏的通道。汉使到达滇池区域十多年间,一直未能打通前往身毒国的道路,受到滇国周围部族的抵抗。在元封二年汉武帝派出兵力强行开道,大将郭昌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迫使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令复率其民。汉武帝苦心打通“身毒道”,历经挫折后,终于获得成功。从此结束了云南割据一方的历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也正式打通了通往缅甸、印度的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由此进入史册,就此拉开丝绸之路的文明进程。
中国于19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份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已存在。
方国瑜先生从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中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蜀身毒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2),汉使张骞向汉武帝报告时就已推断蜀身毒道的存在。季羡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也谈到了“蜀身毒道”: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该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考庇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支那成捆的丝”,而季羡林先生解释成此为“来自中国成捆的丝”。他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认为:“中国地的丝织品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一条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在形成规模通道以前,民间一定相应存在了一些较为方便的交通网络遍布各乡村小镇,尤其当两端之间存在有必要的交换物资时,路途通道也就应运而生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网状的乡村线路就会演变为商道,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会演变成为官道。发端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蜀身毒道”不是没有可能,随着考古发现的推进,时间还在前移。
在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中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说明此时该通道已非常成熟,运输品种多为奇货珍宝,交易终端远达欧洲,为南方发展贸易经济提供了较为便捷的条件。《三国志》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永昌是东汉初设置的郡县,为今日之保山地区一带,《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其边界与缅甸接壤,时至今日任然是云南通往外界的门户,从疆域来看那时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属于哀牢国(古哀牢中国接巴蜀,外壤缅甸、印度,是中国与印度经济文化的连接地带),即后来的上缅甸部分属于永昌辖地。“永昌出异物”,说明那时已有来自于缅甸、印度甚至于大秦(古罗马)的异域商品,西南商道已经出现。
南方丝绸之路既是民间商道,同时又是使节往来、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文化通道,还是与中央王朝得以维系上下关系的政治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一条纵贯东西南北的大通道,道路不断延伸,如网状遍及周围各地,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丝绸、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与内地的物资交易。曾经繁荣兴盛的南方丝绸之路同样也遭遇了不可逆转的挑战,道路改道,南方丝绸之路逐渐被214、317、318国道、铁路甚至航线所取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南方丝绸之路逐渐沉寂,只有为数较少的村寨之间还有少量使用。
茶马古道
据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记载,南方丝绸之路运输的物资中除了丝绸,还包含了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
随着此道物资的转运,从最早开始的土特产品到丝织品的发展,到唐宋以后,茶叶贸易份额加大,因此茶马贸易逐渐加重份额,古道上茶叶、马匹成为交易的重心,茶马交易成为贸易的象征。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输出,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上的市场繁荣,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到了唐宋时期,茶饮大量传播至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及吐蕃藏区,尤其是茶叶被藏族同胞大量接受后,西南商道则更多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如此,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滇川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随着马帮转运,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形成了一条以茶马贸易为代表性的商道,即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首先是与茶有关,其次是与马有关。云南盛产云南马,该马种素有体质结实、短小精悍、运动灵活、善登山越岭、长途持久劳役、耐粗饲、有良好的适应性等特点,受到中原战略物资的青睐。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蛮马出西南诸番……大理马为西南番之最。”蛮马和大理马都是当时滇马的别称。明代设军马场于永胜县。宋代以来,滇马仍不断向省外输出。事实上,茶马贸易是对整个西南贸易的统称,茶、马则是贸易的象征性物质,行走的古道也称之为茶马古道。
从近现代的资料反映来看,茶叶、马匹贸易利润并不可观,但这与茶在另一端藏区或是西北游牧民族居住区域的特殊地位有关。茶在此间区域是稀缺的物资,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而马却是中原重要战略物资,为得到马匹这一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自宋以来逐步设立完善了茶马司,茶马成为国家管控物资,以此羁縻地方势力,因此形成了“茶马互市”,达到统治者“以茶治边”“以茶驭蕃”的目的。中央王朝在西南成都、广西、云南等地设立了规模较大的马市,在茶区又推行了榷茶制,以保证这些物资的顺利管控,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意图,茶马司也成为帝国的隐喻。作为商家可以从中谋利,不必担忧商品的出售,这就意味着两地物资贸易有了足够的保障,因此茶马在整个贸易份额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是交易的中介,也是灵魂之所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南方丝绸之路上逐渐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南丝路再一次以运输货物为标志也被称为茶马古道。
随着时代发展,在古道上转运的物资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转运土特产到后来的丝绸,从唐宋以后,茶逐渐进入该道,当然这时期也包括有丝绸、布匹、马匹、盐、土特产品、药材等等商品,其中茶、马是较为重要的输出和购进的物资,这些物资连接着两端的贸易,也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国西南地区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线性文化遗产。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开始致力于茶马古道的认定,木霁弘、陈保亚等专家学者对滇藏、川藏古代马帮行走路线进行了学术考察,在一路探察后,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在随后的学术研究、推介中得到了普遍认可,茶马古道被确认。
主要路线

平乐镇南方丝绸之路遗址公园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但只是推测,并无考据。一般认为,这条通道正式从西汉开通,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翻越蜀道,至成都,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又称“五尺道”,从东道物资集中地——僰道(今宜宾市)出发,经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一路向东南入越南,并在大理与“旄牛道”重合。相传,“五尺道”由安阳王率领将士和士兵3万多人所开通,他们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史上称其为“蜀朝”。
丝路文化
南方丝绸之路东到中原,西达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过这条道路相互交流,并通过这条道路对西南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考察这条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浓郁的商业性

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民间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兴,也因商得以流传,最后也因商被遗弃。浓郁的商业性特色,可以从几方面得以证实。首先,开辟古道的是经商的人和马帮,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通过“古道”,秦汉时巴蜀的铁、布、朱提的银,邛都的铜,贩到南中,而南中的笮马、僮则贩到内地;唐代南诏时,在古道上进行的贸易逐渐频繁起来,南诏的河赕(今大理附近)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之一,当时印缅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有毡、缯布、真珠、海贝、琥珀等,而从中国输出的有丝绸、缎匹、金银等;元代开滇数百年间,缅北的珠宝、玉器、玛瑙、琥珀成为内地商人争购的商品,因此古道上流通的主要商品便是玉石;明代中国通过古道输往缅甸的最主要的货物为食盐,缅甸输入中国的最大宗商品是棉花;19世纪中叶,中国最需要的缅货仍是棉花,缅甸最迫切购买的是中国的生丝,通过古道输出的商品有生丝、黄铜、雄黄、鞋子、药材等等,输入的商品则是棉花、象牙、燕窝、鹿茸、翠玉、琥珀、宝石、名贵蛇蚊石等。各地商品在古道上流通首,古道也主要因商贸而存在,成为商品的载体,发挥着其流通商品的功能。
其次,围绕古道,从商者甚众,由于商品流通量较大,且绵延不断,有利可图,因此沿古道各地从商者很多。汉晋时,永昌(保山)就云集中国外商贾,不少身毒(印度)商贾和蜀地工匠侨居于此,一些中原派来这里做官的人,也可以在此谋得富及十世的财富,《华阳国志 . 南中志》载:“益州西部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载:“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之民即印度人,骠人即缅甸骠国人,可能就是当时最早的印缅从商侨民。
第三,商贸已具一定规模,沿途商城兴旺。1980年,云南文物学古研究所在剑川鳌凤山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了海贝,其年代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1979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基中,出土海贝1500多枚;解放后在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贝,就达1230多斤,计247000多枚;在腾冲宝峰山核桃园还出土了汉代五铢1000多枚。考查钱币的出土,不难看出,发现古币的地方,往往与商道有关,离古道越近,出土的货币越多,离古道较远,则发现的较少,这些从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舶来的海贝,从战国到明末清初,作为货币使用已绵延2000多年,它不仅是古道沿线各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的见证,而且也是古道沿线商贸较繁盛的见证。
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随文化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古代市镇的形成和扩大。如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公元前4世纪,蜀地的商队就驱赶着马带不断经过这里。公元8世纪,南诏建立,大理不仅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中原严正王朝从南方通往中印半岛直至欧洲诸国的最大口岸,成为中中国地与印缅诸国物资交流的最大集散地,是南方丝绸之路最大的贸易枢纽。古道的商业性特色,使古代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如川西的蜀国、川东的巴国、黔西北的夜郎国、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国、以大理为都城的南诏国等,都建立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并循古道的走向形成市镇网络,而又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效应,形成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
独特的地域性
“蜀身毒道”由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组成。灵关道历史悠久,道路奇险,从蜀地出发,经临邛、灵关、笮、都、泸沽、登相营古堡、邛都、盐源、青岭、大勃弄到叶榆,一路或峰巅嵯峨。
独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点。面对西南横断山地,江河横横溢,山峦叠障的特点,西南各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桥、栈道、马帮。“笮桥”是当地笮族人创造的一种飞跨天堑的索桥,《元和志》卷32载:“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处。”最初采用当地出产的笮、藤拧扭而成,系于河谷两岸,借助木制溜筒,将人畜滑向对岸,以通往来。“栈道”有土栈和石栈,土栈修于原始茂密的森林山地,铺木为路,杂以土石。石栈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孔,孔中插入木梁,上铺木木板。笮桥和栈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这备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胆魄,别出心载创造出来的交通奇观。如果说北方丝绸之路是由沙漠之舟——骆驼开拓的,那么南方丝绸之路则是由山地之舟——马帮开通的。马是西南与内地贸易的重要物资,也是石道上最为常见的,效力最大的运载工具和经商工具,在望不断的崎岖山路上,终年有走不尽的队队马帮,马帮驮来了商品,驮来了文化,交流了友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马帮文化。
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点的又一体现。“其价如金”的蜀锦,质地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泽,在汉化已生产空前,隋唐时规模更大,质量之佳,蜚声于世,堪称东方一绝。西方人正是通过丝绸这一商品开始认识中国,认识东方文明的。铜鼓是亚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源于滇西楚雄,据对万家坝出土铜鼓的测定,其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自创世以来,便进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无论节日、出征,还是播种、丰收、人们都以铜鼓作伴,并由于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工匠和生产技艺为一体,在古代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城乡,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繁衍生息,成为民族性特色极强的地方文化。
明显的融合性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联结中原,沟通中印,它为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丰富的、独特的并且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在古道沿途很流行,在文化发达的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都较盛行,尤其在大理,宋时达鼎盛时代,“苍山与洱海,佛教之齐鲁”,“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鸣钟”。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记行》中说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劳钦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禅记。”佛教的传入,使云南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也融进了佛教文化,为吸引更多的信徒,人们更运用原有的绘画技巧和雕塑工艺技术来表现佛的威力,弘扬佛法,于是在滇池和洱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石刻雕像,如剑川石钟山石窟、剑川金华寺山摩崖石刻、禄劝密达拉摩崖石刻、晋宁摩崖石刻、安宁法华寺石窟、凉山博什瓦黑线刻画像。这些带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无疑给西南地区增添了一枝异彩独放的奇葩。
其余如印度人民互相泼洒净水,祝福祈丰的习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过古道传入云南,成为傣族泼水节的来源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较广泛的祭柱习俗的来源。
中原文化在古道沿途落地生根,如鼎,众所周知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器械,多为铜制,而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味县的古代民族,也同样使用鼎,与中原所不同的是多为陶制鼎。丰满于中原的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据《华阳国志》载,汉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龙纹以为龙子,甚至在古代印度的岩画上也有龙的形象,缅甸、越南、泰国、老挝一些民族中也有纹身刺龙的习俗。
丝路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饶宗颐、云南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均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进行了研究。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南丝路的研究从1980年代逐步开始形成风气,出版发行的研究论著和一系列学术活动、宣传报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丝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早于曾由季羡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所提公元前5世纪,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所提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
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所著书,说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学术界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中国四川。[1]
2000年以后茶马古道随着普洱茶的声名鹊起在几年间起起落落,2001年西藏昌都率先推出关于茶马古道的旅游品牌,并联合茶马古道上的甘孜、香格里拉联手组织了“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邀请到了来自中国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民族学、历史学、藏学、地质学、动植物学、旅游生态等学科开展了广泛的讨论,达成了共识:
第一、茶马古道主要穿行于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唐宋以来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
第二、茶马古道是西南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历史见证,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
第三、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险峻的驿道,部分路段还在运行;
第四、茶马古道沿线拥有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东亚植物区的核心地带;
第五、茶马古道的研究和旅游开发对沿线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次会议召开后,人们对茶马古道有了全面的认知,无论对其开展研究还是发展旅游休闲度假经济,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5年普洱茶热初见端倪,随着普洱茶热,茶马古道也随之再度受到关注。2007年后文物部门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云南、四川、西藏等省区都专门设立了茶马古道调查研究专题,进一步摸清了茶马古道的走向、线路、分布、相关文物遗迹和周边环境风貌等情况,为下一步文化保护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研究方法和视野问题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0公里”地标碑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应以现代化的新视角和全球化的开放视野,审视南方丝绸之路及其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研究重点,应以文化板块的研究,民族相互交往、融合,城镇市场网络体系,整个线路系统为主。具体方法上,可以将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进行对比研究。比如,由于南方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深山里,他们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和交通工具和北方少数民族完全不同,因此两者在贸易方式和文化交流方式上并不相同,值得深入研究。
性质和历史作用问题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始于先秦、盛于汉唐的商贸通道,由多条主干道和支干道组成的商贸道路网络系统,同时也是一条民族迁徙的走廊。从政治上看,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权威达于各地,因此需要开发这样一条通道;从军事上看,为了军队的进入和军事物资的运输,也需要开通这些道路。南方丝绸之路对中央政权统一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陲、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作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青铜文化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对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问题
南方丝绸之路沿途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佛教文化、毕摩文化、东巴文化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均属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遗产历经千年,应充分的发掘、保护与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多功能古道,数千年来留下了无数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和宗教等多重价值的遗存,将其列入“丝绸之路”整体申遗名单,既有利于加强中国段沿线各省市的合作,也有利于沿线国家经济文化和睦邻关系的发展。部分恢复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原貌,尤其是恢复“牦牛道”和“五尺道”的部分景观,并以文化旅游线路整合沿线资源,打造精品路线,推进沿线旅游区域的合作,借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之名,打造新的西南丝绸之路,可以促进西南各地旅游、经济、文化等发展。
历史价值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内接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是佛教南传、藏传,本土宗教的交汇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杂居交错的民族聚落,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从文化线路上来说,这些区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藏彝走廊”地带,也是王铭铭教授“三圈说”的“中间圈”区域。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一方面跨境而居,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语言上交流通畅;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遥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在政令上畅通有效,儒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通过人员交流、物品交换,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圈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处于“中间圈”地带上少数民族是主体,但长期与汉族杂居交融,贸易的终点又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范围内,构成了“边缘”与“中心”的互动。
南方丝绸之路是多国、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特产。它对外来文化既没有照搬、移植或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转运于不同时空中的丝绸、茶马,一路适应、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断地适应中变迁,不断的创造再生,将圈内圈外的文化勾连融合,浑然一体。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四川和云南考古发现的来自西亚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1]
西方考古发现,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发展年代上吻合。
西方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来自古蜀地的产品。由此可知,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埃及,这条路线正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西传的交通线。古代巴蜀丝绸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丰富了印度、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而这条因丝绸传播而形成的线路,不仅对中国早期西南地区的经贸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的经贸繁荣也有较大的影响。[2]
不仅如此,南方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显示,自夏、商时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区迁移,此后这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达到高潮。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达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民族的迁移打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进了文化交融。
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这种创造性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放精神的必然产物,沿线文化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现,是该线路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整体性的象征。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已渐渐转型为象征精神,马帮终将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消逝,沿线旅游、博物馆,茶叶交易新市场等,无不是以茶马文化为内核的发展开拓,而这些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继续传承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