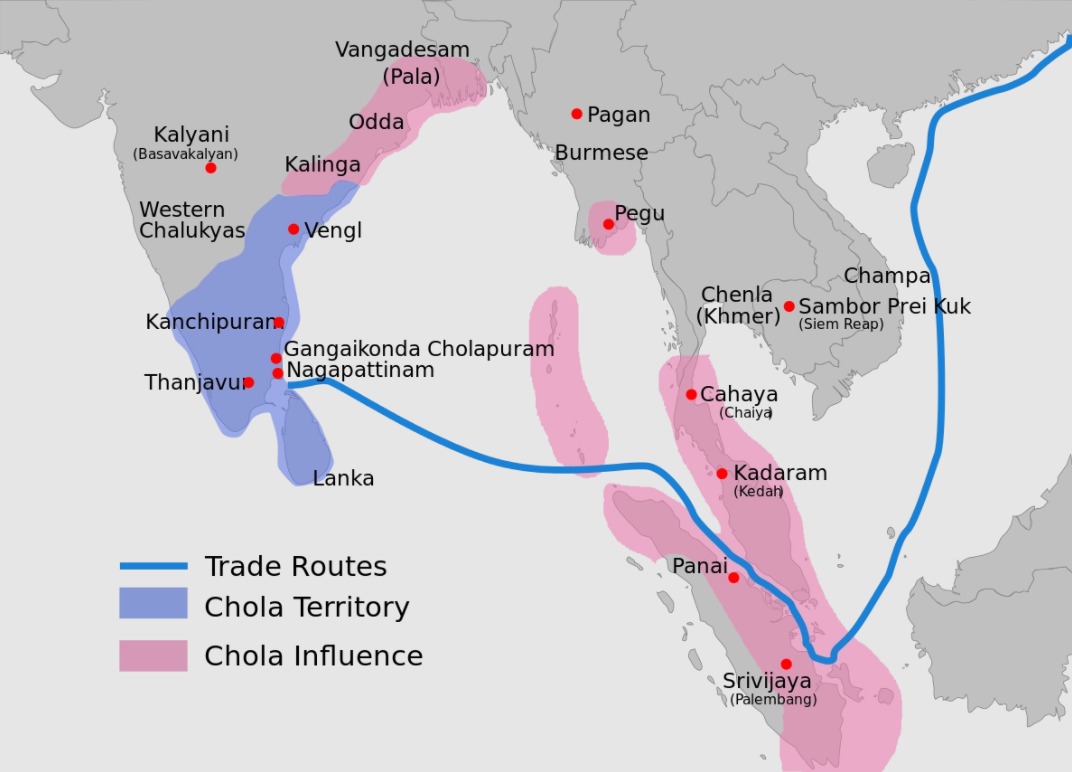节目简介
传统相声《卖挂票》是相声艺术大师马三立的代表节目。五十年代后期,马三立、张庆森曾在天津市曲艺团搭档并常演此段相声,深为相声迷们熟悉和喜爱。
说到传统相声《卖挂票》,不能不先说一下“买蹲票”这件实事儿。在由王决、汪景寿、藤田香所合著的《中国相声史》的“杰作探源”一章中记述“买蹲票”时说:
1931年《戏剧月刊》第五期刊登郑剑西的见闻录,介绍了这么件事:“谭鑫培晚年,除了堂会,戏馆子是不大露的。忽有一次广德楼日戏,贴他的《碰碑》,午后一点正经把戏园子四周上下,挤个水泄不通。好些人来不及吃饭,买了点心充饥,还不敢喝水,怕解手,就不能再占老地方啦!饶是这样,一张条凳还是挤好些人。只要有好戏听,也就不觉其苦。我的朋友石君那天坐在池子里,越到后来人越多,连窗户上都趴满了。

卖挂票
戏唱到“大轴儿”,天也黑下来了,谭老板大概还没有来,台上垫些个《逛灯》、《请医》一路的小戏。这时候,又有一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儿,抹着一脑门汗珠,挤进小池子来找座。伙计说:“这哪儿还有地方啊?桌子上都没有放茶盅的地方啦!”那老头子四下里看看,也真没办法,可是眼看好戏快上了,又舍不得走,没奈何,就跟我的朋友石君商量:“您劳驾就请抬一抬腿吧!”石君问:“干吗?”他说:“让我蹲在桌子底下吧,反正有的听就得听,劳驾,劳驾!”石君瞧他这么大岁数,央告得可怜,就让出一条腿来,让他猫在地下。他谢了又谢,蹲下去了。好容易等到快八点,台上七郎的魂子上了,台底下那么些人,立刻鸦雀无声。那个老头子半天不言语,这会儿却拍着石君的大腿说:“劳驾,您把腿往回靠一靠。”石君以为他闷在桌子底下受不了啦,就想让他透透气。
正说着,堂鼓响了,接着起冲头、导板头,胡琴也响了,等到老谭唱完“……黄昏时候”,台底下崭齐的一声“好!”这时,那个老头子早从桌子底下钻出个脑袋来,用嘶哑的声音喊了一声:“好!”又缩进去了。当时把石君吓了一跳。以后,凡是老谭使一个好腔,他就钻出来喊一声,一直到戏打住。
散了座,他才颤巍巍地从桌子底下出来,对石君咂咂嘴说:“真过瘾哪!”石君问他:“累吗?”他说:“不累,听这出好戏,委屈着蹲一下子,也算不得受罪,可是您刚才要不让我把那声好喊出来,那可真憋得我肚子疼呢!”
买蹲票是生活里的实事儿,买挂票也是这样。据《梨园外史》记述:“春台班开戏第四日,胡喜禄唱《玉堂春》。看戏的客座人山人海,后面来的人没有地方,用粗绳子把板凳悬在戏楼的栏杆上,打着秋千看戏。众人不看戏了,都来看这稀奇的“景致”。后来相声艺人把这两件事夸张成“真有一百七十多位没走!墙上挂着呢,走不了啦!”这就充分达到了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境界。
经马三立、王凤山整理并演出的《卖挂票》从作品结构、人物性格、语言心态、包袱处理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镜界。在节目的“垫话儿”里,马三立侃侃而谈,说的是一些戏剧的基本常识,然后很快引出自己的身份。“拿我当杨宝森”一句真是神来之笔,是高妙的自嘲,体现了马三立在相声表演时善于用语言塑造性格人物的艺术功力。“洗澡”与“盛(剩)藻”、“芜湖”与“呜呼”、“导演”与“捣眼”等包袱的安排以及向乙解释戏名与戏中人物时屡屡出错都起到了揭示人物内心、丰富人物性格的作用。
通过观众买蹲票、挂票的自我吹嘘以及自称金少山来拜会并乞求与他配戏还挤掉了周瑞安的饭碗等情节,似乎在力争吹嘘、抬高自己,其实这也是为最后的结局孕育着越来越多的喜剧因素,抬的越高,摔的越重。所以当结尾的一句“墙上挂着,走不了啦!”把包袱抖响时,在观众哄堂大笑声中,马三立完成了他的艺术创造,留给人们的则是笑后的沉思与悠长的回味。
锤炼性格化的语言与塑造性格化的人物是马三立相声的绝妙所在。
节目台词
甲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它的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相声它这里头啊,它也有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市民语气,有地方语,那是很多。
乙 哎。
甲 戏剧就不是啦。话剧呢,它就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啊?那京剧,它就得呀,它单有京剧的台词。它就跟咱们普通话一样啦。
乙 是啊?
甲 哎。别忙——它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
乙 哎。别忙。
甲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这么说?你刚走那儿——“且慢”。可舞台里头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听戏就是“别忙”,让他“打住”。“罢了!”是“得啦!”一见面,请安,“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摆了”。咱平常不用,“老没见,你好啊?我给你请安!”“哎,得啦,得啦!”不能“罢了”!用不上。这舞台上它有舞台词——“罢了”!“且慢”,“呜呼呀”!“呜呼呀”是纳闷儿,“呜呼呀”!不信?“你待怎讲?——你再说一遍——你待怎讲?”
乙 哎。
甲“嘟!”是急啦。“嗯?”是不乐意了,不乐意啦——“嗯?”“嘟!”急啦!这场戏见官儿,给官儿跪下,最好是:“呜呼呀!”这犯人准有好处,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官儿一瞧:“呜呼呀!”行啦。
乙 怎么?
甲 呜呼呀!不像是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啦。“嘟!”——坏啦!
乙 怎么?
甲 倒霉啦!“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嘟!”倒霉,准糟!
乙 生气了。
甲 那可不!这戏剧很深,下功夫最难。“唱、打、做、念、翻”,这个……这个舞台上……
乙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甲 研究干吗?你不认识我?你不常听戏。
乙 那你?
甲 你常听戏吗?京戏,你听不听吧?
乙 我从小就爱听戏。
甲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乙 不认识啊?
甲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我。
乙 是啊?
甲 你怎么不认识我呢?
乙 您是哪一位?
甲 杨……
乙 杨?
甲 杨宝森!
乙 杨宝森?你是杨宝森?
甲 真是不认识,拿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杨宝森哪。
乙 您是谁?
甲 提杨宝森这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乙 知道。
甲 我给他蹬三轮儿。这多少年了吧。
乙 多少年了?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儿啊!
甲 那玩艺儿!
乙 那玩艺儿也是蹬三轮儿啊。
甲 他蹬三轮儿,蹬我。
乙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儿啦?
甲 拿你当三轮啦!我坐……我坐那儿,蹬三轮儿那蹬着,后来我让他,“你蹬宝森吧!”宝森净闹病,车是我的,我送给宝森。
乙 啊,送给他了。
甲 我不姓杨。
乙 哦!您是?
甲 马!北京你打听打听!北京你打听打听,唱戏的马老板!那谁不知道啊?
乙 哦,北京马老板?马连良?
甲 马连良干吗?马连良是我们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乙 哦,一家子。
甲 马连良是“连”字儿的。
乙 对。
甲“富连成”,他排字排“连”字的!我们科班儿,那时候叫“喜连成”,听说过吗?
乙 听说过。
甲“喜连成”!哎,我们“喜”字,雷喜福?知道吧?
乙 雷喜福,大师兄?
甲 哎,对。
乙 知道。
甲 我们一块儿的。这还用说吗?侯喜瑞知道吗?
乙 知道哇。
甲 侯喜瑞——“喜”字嘛,陈喜星、康喜寿、魏喜奎……没有魏喜奎,魏喜奎她改大鼓啦。
乙 没改!第起就唱大鼓的。
甲 不是魏喜奎,什么“喜奎”我忘了。
乙 哎,刘喜奎。
甲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儿的。
乙 哦,您叫?
甲 喜藻。
乙 洗……我修脚。
甲 修脚干吗?
乙 你洗澡干吗?你那儿洗完啦,我这儿……。
甲 喜!排“喜”字儿那个“喜”呀。
乙 那个“喜”呀?
甲 不是洗澡的那个“洗”。道喜、福禄寿喜的“喜”。
乙 噢!澡?
甲 藻是那个……这个字还说不上来。
乙 他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甲 草字头那个……我想想草字头那个。
乙 李盛藻的那个“藻”。
甲 哎,你要是不提,我还把他给忘啦!李盛藻,听过吗?
乙 听过。
甲 唱的怎么样?
乙 好啊。
甲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的,李盛藻唱得行吗?
乙 不错。
甲 你认为怎么样?
乙 都认为不错。
甲 服吗?
乙 服!
甲 那就完了,那咱就没杠抬了。你服,就完啦。那我就……行啦。
乙 我服李盛藻,碍着你什么啦?
甲 你要服李盛藻就行啦,
乙 怎么啦?
甲 你认为盛藻好,那就成!我痛快。
乙 与你何干?
甲 他跟我学的。
乙 李盛藻跟你学的?
甲 有人听过吧?李盛藻唱的怎么样?他完全学我,也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在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是我教的,完全学我。
乙 是啊?
甲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的戏一样。李盛藻——我给起的名字,在科班他排字排“盛”字儿。我说他叫“盛藻”,你就知道跟我学的啦。
乙 怎么?
甲 我叫“洗澡”嘛,他叫“剩澡”——我洗剩下他再洗!
乙 好嘛!俩人一个盆儿。
甲 我总在江南,江南一带。上海到过吗?
乙 到过。
甲 南京呢?
乙 到过。
甲 到南方你打听打听,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喜藻,我!嘿,镇江,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乙 是啊?
甲 苏州,我。
乙 哎哟!
甲 我……杭州。
乙 好。
甲 ……芜湖……我,我快啦,快啦!
乙 快“呜呼”啦!要死了这位!
甲 我说我要死啊?我说我要死啊?
乙 不你说你快“呜呼”了吗?
甲 我快到芜湖那地方去啦。
乙 哦,到那儿演出。
甲 我现在不演出,我这些年不唱啦,气的!我生气,不唱啦。
乙 跟谁呀?生这么大气?
甲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一九……我想想啊,一九四五年,你看这多少年了吧?
乙 日本降服那年。
甲 哎,对啦,日本降服,一九四五年。
乙 跟谁呀?生这么大气?
甲 那时候,我在那儿教……教票友,现在不叫业余吗?那时候就是票友。
乙 对对。
甲 国剧社。我呀,我在那儿当教练,教练,我教练。
乙 教练?足球啊?是排球啊?
甲 足球干吗呀?我唱戏!足球干什么?
乙 不是教练吗?你也唱戏?
甲 不是教练……我……我叫指挥,不叫指挥,我把场子,服务员把着。
乙 什么呀?
甲 把场子。
乙 把场子也不对呀。
甲 我得听,我得排!
乙 那叫导演。
甲 对,对!导演。我给你导演。(冲乙捣眼)
乙 别!一会儿瞎啦,你给我捣眼?
甲 我去那儿当导演,我给排戏。
乙 噢。
甲 票友跟我学。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您学差不离,几年啦!每月给您这么些钱,天天管您饭,请你舞台上,你给看看。没见过您走台,您演两场,看看您舞台身段儿,跟您学学。”
乙 哎,让你演演。
甲 很多票友,要跟着学,要看看舞台经验,看看咱舞台表演,怎么办?
乙 那……演吧。
甲 唱吧。
乙 哎。
甲 咱不为赚钱,就为了让票友学。
乙 对对。
甲 演两天儿。
乙 在哪儿?
甲 在黄金。
乙 黄金大戏院?
甲 啊,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演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演两天,票友们学,这不订好了吗?该着你生气。
乙 怎么生气啦?
甲 唉!那年啊,那年哪,那个谁呀?小云儿啊!他呀,这番儿……
乙 哎?小云儿是谁呀?
甲 尚。
乙 尚小云?那是尚老板!还小云儿呢?
甲 尚小云呢,他这番儿啊,到上海,黄金戏院——他唱啦!又改他唱啦!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儿,我一看:黄金大戏院门口贴着这么大的大宇:“尚小云。星期六开始演
出。”我一看,哎?咱定好啦——礼拜六、礼拜呀?
乙 就是啊。
甲 怎么改啦?我问问这个经理,怎么办?
乙 得问问。
甲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说经理呢?经理呢?”经理在屋里坐着呢,“啊,来,来!进来!正要找你,不知你哪儿住。”
乙 这角儿,没准地儿。
甲“你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不是订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尚老板来啦。”我说:“哪个尚老板?”“尚小云——尚老板。”“那么我呢?”“你听信儿。”
乙 听信儿?
甲 我说:“听多咱的信儿啊?”“听信儿!多咱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乙 好嘛,这位是打补丁的。
甲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你就信他呀?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乙 你非唱不可,那不给人尚老板开搅了吗?
甲 我搅和他干吗?我非得黄金大戏院呀?
乙 哎……对。
甲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学的?真是!天蟾舞台。
乙 天蟾大舞台?嚯?最大的。
甲 对啦!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乙 比他多一天。
甲 咱赌这气儿,戗这火。多演一天,我演三天。
乙 演三天。
甲 瞧他票价卖多少钱?跟他比着。打听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票价?一打听,尚小云那儿——八千块!
乙 八千?
甲 前排每座八千块!一九四五年。
乙 可不多。
甲 贵啦!大发啦!大发啦,高啦!价码高啦!
乙 买个烧饼还一百块钱呢,尚老板卖八千块儿?
甲 不值,不值。
乙 太贱啦。
甲 这不天蟾舞台跟我商量了,咱这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他说“八千。”那儿八千,一想啊,我这儿啊……甭犹豫,干脆!
乙 两千块钱儿!两千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不为听戏,为喝茶……对不?
甲 谁呀?谁呀?你说谁呀这是?谁呀?说谁哪?
乙 说你呀!
甲 八千,那儿八千。
乙 八千那是尚老板。
甲 我,我多少钱?
乙 两千块钱,不少啦!
甲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啦?看见啦!你听说的?你看见啦?你是听说啦?你看见啦?你听人说的还是你看见啦?
乙 我这么琢磨着。
甲 呸!要不这种人!你就不能搭理他,你不能理他呢!这儿还慢慢告诉你:八千、八千!他那儿八千!我两千?还带点儿好茶叶、管饭。我跟你要价,我算栽啦,我算栽跟头啦!
乙 哦?那您卖多少?
甲 卖多少钱呢?一万二!
乙 啊?前排一万二?
甲 前排干吗?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一万二。前后排不对号。
乙 一万二?
甲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一万二,后排一万二。楼上、紧后边,照样一万二。
乙 嗬!这价码可高。
甲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的是玩艺儿,听的是戏,咱三天戏码得硬。
乙 哎,头天是什么戏?
甲 啊?头天呢,《连环套》。
乙 《连环套》?
甲“盗钩”。
乙 嘿!这戏好戏。
甲 嘿!《坐寨》、《盗马》、《拜山》、《盗钩》唱全啦!窦尔墩、尚小云来一个?尚小云来窦尔墩?
乙 来不了,来不了!
甲 噢,噢!完了吧!
乙 第二天呢?
甲 第二天呢,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乌盆儿记》。
乙 老生戏?
甲 唱功戏。
乙 老生你也成啊?
甲 也行啊?也行啊!唱、打、做、念、翻,全活儿!
乙 老生,你去谁?
甲 《奇冤报》——老生!头天,我“窦尔墩”!《连环套》。
乙 别说窦尔墩!这《奇冤报》老生是谁啊?
甲 我唱功戏呀。
乙 是啊?去谁呀?
甲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我来一个……
乙 别,别三天!第二天。老生是谁?
甲 我知道。第二天啊,第二天啊,老生啊,谁呢?《乌盆记》嘛,他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做成盆儿嘛。
乙 对对,他叫什么名字?
甲 你瞧,(唱)有那公俺做了……
乙 行行。
甲 别忙,一会儿,这词儿就出来了。
乙 准问词儿啊?问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
甲 徐世昌。
乙 什么?
甲 徐世昌。
乙 徐世昌?刘世昌!
甲 对!刘世昌,刘世昌!对!我说成徐世昌了。刘世昌!
乙 徐世昌?那是大总统!
甲 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好!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红尤二楼”,“红尤二楼”!瞧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顶下来。
乙 一个人顶下来吗?
甲 哎,怎么顶不下来呀?
乙 红油二楼?
甲 哎!
乙 三楼就不油啦?三楼还油吗?
甲 我这……我干吗?我油三楼干吗?
乙 你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甲 这是那戏!这是大楼,什么楼……那戏!
乙 那是《红楼梦》,尤三姐、尤二姐!
甲 我知道,你甭管,我就来这个。头天的《连环套》,我唱晚场戏,白天我不唱。
乙 白天不唱?
甲 晚场戏。早晨,八点来钟,客满!剧场,坐满啦!
乙 晚场戏,早应该坐满啦!
甲 不对号啊,不对号入座,谁不得早去呀?赴前排座儿,得听得看哪。
乙 对对。
甲 都早去呀。观众去得早,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得着着的,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扒开门一看:嚄!我心里话!
乙 哎哎!等等!八点应就满了,你怎么知道的?
甲 这,正把我吵醒啦。
乙 把你吵醒啦?你在哪儿睡觉啊?
甲 后台。
乙 哈哈,后台睡觉?你住旅馆、饭店哪?
甲 我不住饭店,我就住后台。我总住后台,我总跟箱官儿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箱官儿。
乙 你干吗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甲 我就为盖他的被卧。
乙 嗬!这角儿!连被卧都没有。
甲 不是没有,不是没有!
乙 有?
甲 我有钱不置这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儿,带着麻烦。我有钱,我多置行头,门帘、大抬杠我有七十多个。
乙 七十多个?
甲 哎。
乙 你改俩被卧好不好?
甲 管得着吗?我乐意呀!我乐意呀。刚顶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四百多位,买票。前边不能卖票啦,座满啦!没票了。“没票啦?不行!我们也得听啊!我们听马喜藻马老板,
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打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家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瞧,这么多人,怎么办?没地方坐啦!“买站票吧!”“站票?行!”“一万二!”
乙 啊?站票也一万二?
甲 照样一万二。四百多位,愣屈尊大驾站着听,太好啦!太捧马喜藻啦!太捧戏啦!站着听,四百多位。刚站好,又来了,又来三百多位,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
呢?站票都满啦,您买蹲票行吗”?“我们乐意,乐意”!
乙 蹲着?怎么蹲?
甲 人都上边宽底下窄呀,两位的空档蹲一个,两位的空档蹲一个。
乙 好嘛!受罪来啦!
甲 哎,刚蹲好,又来一百七十多位!
乙 一百七十多位?
甲 这一百七十多位在门口直哭,直掉眼泪。“我听不着马喜藻,简直活不了啊。”
乙 哎,至于吗?这个!
甲 哎呀,经理心软啦,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乙 挂?怎么个挂票?
甲 就一棵绳子拴一个,一棵绳子拴一个,往墙上,往墙上一挂。
乙 好嘛!受罪来啦?
甲 挂票!挂一百七十多位!
乙 好!
甲 嗬!我心里这痛快!扮戏呀,窦尔墩!刚要打花脸儿啊!
乙 哎!那叫勾脸儿。
甲 我说勾脸儿怕你不懂!勾脸儿……勾眼儿?
乙 勾脸儿!
甲 刚要勾脸儿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戴着黑眼镜儿,茶镜、墨镜,咱说不清楚啊,大个!“哦,辛苦,辛苦,辛苦!众位!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藻?哪位洗藻?”
乙 好嘛,找洗澡的!
甲“我,我!我,我姓马!”“哦,你好!实在该来啦!少拜望!不知你哪儿住!”
乙 噢?谁呀这是?
甲 不认得。“你干吗的?唱戏的?不认识啊,贵姓?”“金、金少山。”“少山?”
乙 金少山来拜望?好!
甲“啊,您找我?有事儿吗?”“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非唱《窦尔墩》哪?你要唱窦尔墩,我就没饭啦!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一带,我小小有‘蔓儿’,都知道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听我那个,我一分钱不值啦!无论如何,你赏我点饭吃,我来窦尔墩。”
乙 他要来窦尔墩。
甲 我说:“你来窦尔墩,我呢?”“您来天霸?”“谁?”“我少山来窦尔墩,你来天霸。”
乙 天霸,你也行?
甲 也行?把“也”字去啦!就是“行”!我说:“好!你扮吧!我给你画脸儿。”“哟!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窦尔墩,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
乙 瑞安是谁呀?
甲 周瑞安,周瑞安都扮好天霸啦!我说:“你算了吧!你改弃权,我天霸。”我扮好了天霸了。我扒台帘儿一看:少山这……这窦尔墩啊!
乙 那是真好!
甲 一文没有啊。
乙 啊?
甲 《盗马》的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一点也不一样。
乙 是啊!他要跟你一样?他也没被卧啦!
甲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他唱的《坐寨》,那摇头、晃脑地一唱,谁给他叫好?打他一出场,那台下的观众就嘀咕:“嘿!好啊,好!马老板呢?马喜藻!”“金少山哟?”“马老板?一定‘天霸’。”都憋着给黄天霸叫好!
乙 听你的。
甲 听着咱这一上场,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来怎么样?
乙 猴儿啊?
甲 好,句句落好。他不落好,咱还不落好?他唱的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也不知怎么啦!
乙 是啊?
甲 那天我不知道那天我吃了什么啦?那天,嗬!我嗓子这个亮啊!(学唱)“一马离了……”哎?不对。
乙 不是这词儿。
甲 这是《汾河湾》啦!
乙 什么《汾河湾》?
甲 《武家坡》啦!我是“宝马?”我是“保镖……保镖……”什么?
乙“保镖路过马兰关”。
甲 哎?那天你听啦?
乙 我没听!
甲 听啦!听啦。
乙 我没听。
甲 没听,你怎么把我词儿给记住啦?
乙 你的词儿?
甲 我就这词儿。
乙 谁唱都这词儿。
甲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保……”
乙 保镖!
甲 哦,对!(学唱)“保镖路过马兰关哪,啊……!”一落腔,底下这观众,连楼上、带楼下,哗!
乙 你瞧这好啊?
甲 全走啦!
乙 那还不走?
甲 骂着街地退票。
乙 好啊!
甲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咱这玩意儿,货卖有识家。
乙 对。
甲 真有一百七十多位没走!
乙 爱听?
甲 墙上挂着,走不了啦!
乙 走不了啦?
马三立 王凤山演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