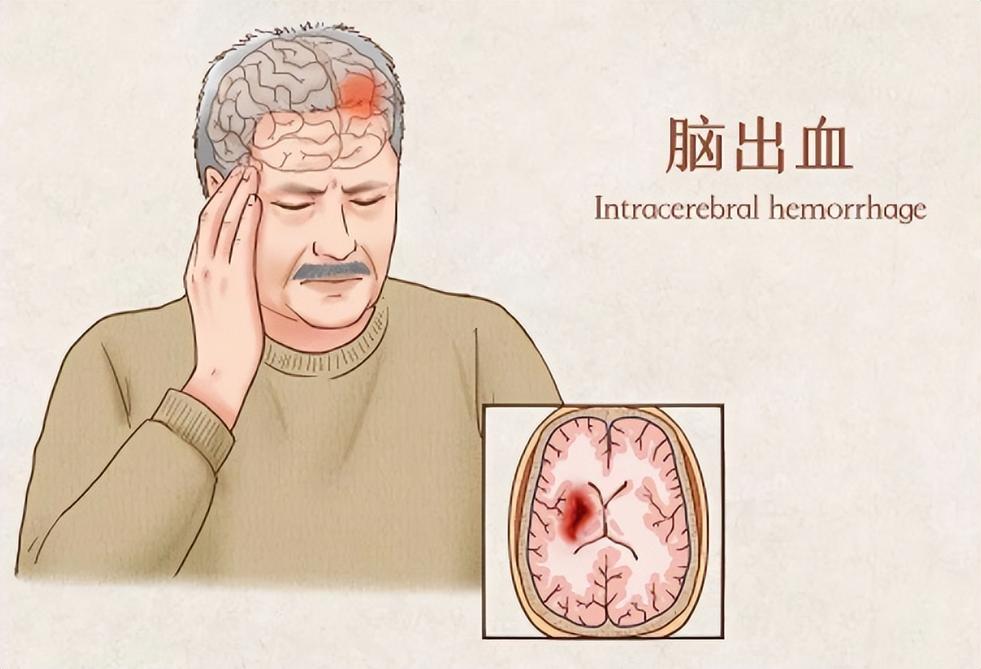背景
二十三年,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兰丹,曰那旺,曰丁呵儿,曰来来,曰急兰亦曈,曰苏木都剌,皆遣使贡方物。
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时方议征爪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并为平章。诏军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谕之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力也。”军次占城,先遣郝成、刘渊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不鲁不都、八剌剌诸小国。
三十年,攻葛郎国,降其主合只葛当。又遣郑珪招谕木来由诸小国,皆遣其子弟来降。
元朝当时几乎在东亚东南亚都有属国,对于这样的庞大势力常人早就臣服投降了。
高丽归服明朝后不久,朱元璋对来明的高丽使臣张子温等说:“昔日好谎的君王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有,我这说的话,你去国王根底明白说到。”后来他又谈到,“曩者中国历代,数曾统驭,然兴彼当时之人,皆有始有终,得失载于方册,朕所见焉。所以前者命绝往来,使自为声教,以妥三韩。”至于如何处理好与高丽的关系,朱元璋同样吸取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若汉、唐之夷彼,隋君之伐东,在朕之今日,非诈侮于我,安敢违上帝而劳扰生民者乎?”因此他想仿效上古之君“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令土人主之”,自己“虽不才”,但能察“圣人之心”,欲体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不劳夷民。关于这点,朱元璋在后来与高丽的实际交往中,确实也履行了。洪武十九年(辛禑王十三年)五月,朱元璋与高丽使者说到:
“耽罗(今济州岛)我也想教些船去,不要一时抛在那里。只离那里二十或三十里,往来周回枪着,逐一个抛者买了便回来。我又寻思不便当,恐又生出事来,不免又动刀兵,以此不买去了。原(元)朝放来的马,只恁管,我不差人。我要差人时,一头得了大都,便差人管去了。大概人不才的多。若差一个不才的人到那里,那厮倚着朝廷的势力,倚恃着朝廷的兵威,无所不为起来,便是激的不好了。我决然不差人,却也地面近恁那里,和罗州厮对着,从来恁管,只会恁管。我常想汉光武时,四夷请官,光武不许。盖是光武从小多在军旅中,知道许多弊病,所以不许他。这是光武识见高处。后来的君王多差了。便如高丽,也都分为郡县,设置官守。后头也是那不才之人,恃倚朝廷威势,做的不好,都激变了。却因朝廷事多,就不暇整理他了。”
可见,朱元璋从以往经验中得到启发,不想直接介入高丽内部事务,而想“丽人治丽”,最终两国关系稳定,百姓相安。
然而,在这问题上尽管朱元璋显示出极大的善意,也没能让高丽完全断绝与北元的关系,一心一意地归服明朝。这是朱元璋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高丽杀明使、刺探军情等一系列做法让朱元璋极为愤怒。在给高丽的国书中,朱元璋明确表达了他的想法:
“朕观高丽之于中国,自汉至今,其国君臣,多不怀思,但广诈交而构祸,在昔汉时,高氏失爵,光武复其王号,旋即寇边,大为汉兵所败。唐有天下,亦尝赐封,随复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绝。迨宋之兴,王氏当国,逼于契丹、女真,甘为奴虏。元世祖入中原,当救本国于垂王,而乃妄怀疑二,盗杀信使,屡降屡败,是以数遭兵祸。今王颛被弑,奸臣窃命,将欲为之,首构雠怨于我。……朕观此奸之量,必恃沧海以环疆,负重山固险,意在逞凶顽以跳梁,视我朝调兵如汉唐。且汉唐之将,长骑射,短舟楫,故涉海艰辛,兵行委曲。朕自平华夏,攘胡虏,水陆通征,骑射舟师诸将岂比汉唐之为。
高丽隔大海,限鸭绿,始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盖为所生鸒端。朕观累朝征伐高丽者:汉伐四次,为其数寇边境,故减之。魏伐二次,为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故屠其所都。隋伐二次,为其寇辽西,阙蕃礼,故讨降之。唐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兄弟争立,故平其它,置为九都督府。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元伐五次,为其纳逋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
朱元璋在与高丽的交往中自己得出了历代君王征伐高丽(朝鲜半岛)的原因,他认为是高丽君臣不怀思,广诈交而构祸,一切皆为高丽之自取,而不是中国帝王好吞土地。这显然只是朱元璋从自己的角度来说的,但也确实反映了他“善意”得不到回报时的气愤与归服高丽的决心。同时,朱元璋还总结了以往汉唐征高丽失败的原因,并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十分自信,目的是想告诉高丽国王:并非明朝没有力量攻打高丽,只是他不想这样做而劳扰生民。为了强调这点,朱元璋还曾对高丽国王说:
“今番兀都那云南,我本不征伐他;他却如常生边鸒,以此无乃(奈)何去征他。一万里远,接连着吐番一带,用热多军马去守,又无益于中国。征伐之事,盖出于不得已。……若不至诚,不爱百姓,生边鸒,这等所为呵,我却难饶你。我若征你,不胡乱去,一程程筑起城子来,慢慢的做也。”
朱元璋向高丽国王提征云南之事,是想说明征伐之事既无益于中国,也有损于对方,他本身并不愿意兴师征讨,只要高丽依守本分,至诚事大,则两国相安。
面对形势的变化,高丽也不得不断绝了与北元的关系,重新恢复与明朝的友好关系。
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告诫其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其后又在他颁列的十五不征之国中,把高丽放在最先。
元朝初期,忽必烈曾经发兵征伐日本,导致日本念念不忘,于是终元之世,日本不与中国同好。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意思是宣告:元朝已经灭亡,现在中国是大明王朝,你们诸国赶紧奉大明为“正朔”来朝贡。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朕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即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既而,西域诸种番王各献良马来朝,俯伏听命;北夷远遁沙漠,将及万里,特遣征虏大将军率马步八十万出塞,追获歼厥渠魁,大统已定。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朱元璋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结果,使者被日本人砍了脑袋。
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贡时,内带行商,私通胡惟庸多行谲诈,故沮之。
面对倭寇的骚扰,明朝的海防政策的基础是1372年发布的禁止海上贸易的命令。皇帝之所以实行这种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他的臣民会勾结中国以外的人民来向他的统治挑战。他相信,室利佛逝国曾派遣间谍来到中国,所以就把它在朝贡名单中勾销。这种禁令由市舶司所实施的管制办法来加以贯彻。
朱元璋虽然一生以军事和政治作为自己的“主业”。但他似乎特别谨慎用兵。洪武二十年十月。在与诸将论及兵政时,朱元璋这般说道:“国家用兵,犹如医生用药。开了大堆的药,目的是要治病,不能没什么病就吃吃药,那可要吃坏的!治国也如此,国家不太平,用兵来勘定祸乱。等天下太平了,只需整修甲兵.操练士卒,备作国防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应该要知道:用兵能消除祸乱,但也能招致祸乱,倘若恃富逞强,好大喜功,惹是生非,就会结怨挑衅,这不恰恰招惹了祸乱!正如医生乱开瞑眩之药,强迫无病之人服用,虽然不至于造成身体残疾或送命,但足以大伤元气!所以为国当政者应该常讲军事,但千万不能穷兵黩武!”(《明太祖实录》卷186)
这是一生讲究“洪武”“尚武”的老辣皇帝的“谆谆教导”,这更是朱元璋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的顿悟。他在南京明皇宫奉天门给各部大臣做了这番告谕:“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指漠北蒙古).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明太祖实录》
洪武晚年,老朱皇帝生怕子孙后代狂妄、轻浮、率意用兵,从而招惹祸害,特地将自己的谨慎对外用兵之国策写入了《皇明祖训》之中:“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接着朱元璋开列了15个亚洲邻国为大明的“不征之国”。即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无故去侵犯。
内容
高皇帝在处理藩属关系上,有很强的华夷区隔的观念。洪武十四年版的《祖训录》说: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可见他认为这些地方不仅人口构成上就是“夷国”,且地理偏僻,不能给“中国”带来实利,他打你可以,之后你可以反击,但不可主动攻打。洪武二十八年版的《皇明祖训》也延续了这一点,更具体地规定了15个“不征之国”。这种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褒华贬夷思想在汉官与汉化官员思想也可以看见。《元史·列传》:“三屿国,近琉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选人招诱之。平章政事伯颜等言:“臣等与识者议,此国之民不及二百户,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去年入琉求,军船过其国,国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无它志也。乞不遣使。”帝从之。”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对明代华夷基调:一要奉行不直属,二则厉行海禁。奉行和平外交是华夏天朝传统的“怀柔远人”之道的延续,也是对蒙元统治者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否定。
影响
史书记载,隋炀帝免费招待“万国宾客”,这些费用一旦皇家结不了账,就要落在店家头上,这简直是皇帝拉着店家一起“赔本赚吆喝”。他死要面子让百姓活受罪,只为换得“名义上的尊重”而毫无实际利益,结果得不偿失。
对于朝贡本质,当时有个意大利“中国通”利玛窦,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
利玛窦是个传教士,在中国前后逗留了28年,对中国国情可谓驾轻就熟。
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
利玛窦在他的著述中写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外交官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中心论。利玛窦说:“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他说得一点不错,中国人“偶而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中国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他批评中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据利玛窦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国人“为了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在通用。”尽管过了4个世纪,“番鬼”这词至今仍在广东话中流行。
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如影相随的,就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惧与反感,以致“从不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正如《中国札记》所说,“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他们祖先的法制。”明朝这种誓死捍卫“祖先法制”的做法,不啻是当今某些鼓吹者的异代知音。
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利玛窦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华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拒绝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推动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中国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渐低落,利玛窦也成为中华帝国文明夕照的最后目击者之一。他在华长达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这里列举的,只是他对明朝人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的细微观察,已让400年后的国人有入木三分的感慨。
《中国札记》英译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尽头,但是无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这一论断,褒贬俱有。从贬的角度说,却让人如芒在背。难道在超阈度的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上,利玛窦所擿发的痼疾仍会旧病复发吗?但愿国人不要让这段话不幸而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