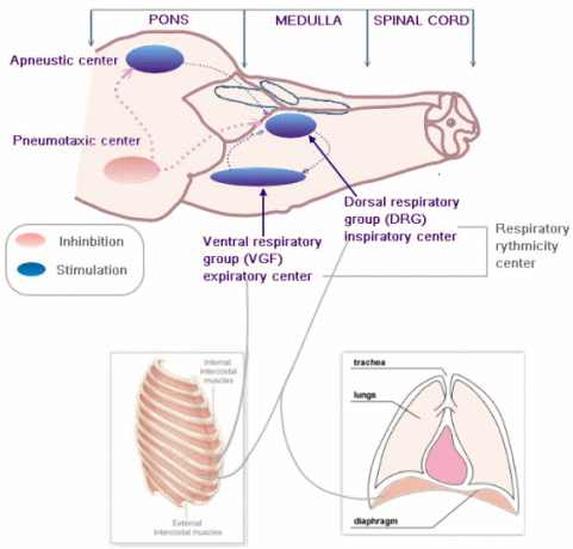简介
属国的设置始于战国,如秦兵器铭文中已有属邦一词。汉避汉高祖刘邦讳而改称属国。据《汉书》卷6《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汉书》卷6《武帝本纪》颜师古注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后汉书》卷118《职官志・百官五》又云:“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可见“属国”是中央王朝为安置归附的边疆民族而依缘边诸郡设置的一种行政建制,“主蛮夷降者”,与郡同级。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到汉末为止,北、西、东三边诸郡:定安、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北地、犍为、广汉、蜀郡、张掖、居延、辽东都有属国的设置,大者领有五六城,小者一二城。大郡割边远县置属国,如割广汉北部都尉所治为广汉属国,割蜀郡西部都尉所治为蜀郡属国,割犍为南部都尉所治为犍为属国,割辽东西部都尉所治为辽东属国。小郡则属国置于本郡之内,不另标名称,如龟兹属国只作为上郡的一个县而存在。
属国设有都尉、丞、侯、千人等官,下有九译令,又有属国长史、属国且渠、属国当户等官。各官由汉人或内属胡、羌的首领充任。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一级,直属中央,其治民领兵权如郡太守。
属国官掌属国兵,称属国骑或属国胡骑,又称属国玄军(玄军即铁军)。张掖属国有精兵万骑。
历史延伸
唐朝廷对来朝贡的国家一般都有相当丰厚的回赐。这种"贡"和"赐"的关系实际是不等价的,对朝廷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朝廷之所以明知亏本而乐此不疲。
唐代"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已经无力再做这种亏本生意,朝贡贸易萎缩不振。于是改变经营方式,产生了市舶贸易。市舶贸易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但是到了明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绝对禁止私人对外贸易,所有的外贸又以朝贡形式进行。随朝贡而来的船舶,称为贡舶。朝廷并规定,东南亚国家一西洋诸国在广州登陆,日本在浙江宁波登陆等。广州是指定贡舶靠岸最多的港口。这种朝贡贸易制度,从明代后到清代,又延续了一百多年。
唐中后期,市舶贸易已经取代了朝贡贸易。
什么叫市舶贸易?市舶贸易就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相当于今天的市场经济,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贸易经营。这种贸易,朝廷和地方都要赚到钱。要管好,必须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朝廷管理。
唐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
市舶使的职责有四条:一是向前来贸易的外国船舶征收关税;二是代表朝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三是代表朝廷管理海外各国朝贡事务,管理外国商人向皇帝朝贡的物品;四是总管海路通商,对市舶贸易朝廷监督和管理。
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的最大成就是,确立起一套全新的市舶管理制度与经营方式,并为后世所沿用,在中国外贸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广州是唐代惟一设置市舶使的城市,为整个国家履行对外贸易的管理职能,具有特殊的地位,在海外享有声誉。当时各国到唐朝进贡,都必须先到广州,广州再选择首领一人随员两人进京,其余随员留在广州。那时,外国人称长安为摩诃支那,梵文意思是大中国,称广州为支那,意即中国。
唐代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转折点,唐朝廷在广州设立了市舶贸易制度,由海道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大为增加。
到了宋代,与广州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于五十个。广州成了"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大批船舶货物从海外运到广州,再从广州运送全国各地。广州的舶货物从海外运到广州,再从广州运送全国各地。广州的舶货除了部分朝廷直接北运外,其余全部在广州贸易,形成广州巨大的舶货市场。中外商人在这舶货市场中获得高倍利润。
1080年,宋朝廷正式修订了《广州市舶条》,并向全国推行。条文主要是关于海舶出入港的管理,征税的新规定,专卖专买的规定等。
优待外商是广州市舶贸易发达的一个因素。如长居广州的阿拉伯船主蒲希密父子和一阿拉伯一百三十岁老人,先后受到宋朝高官的友好接待。
广州市舶贸易量最大的仍是阿拉伯,其次是苏门答腊岛和爪哇。
元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大发展,同中国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原来的五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个。
朝贡本质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尽管中国人拥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和海军,要征服邻邦,轻而易举。但皇帝和人民,都不曾考虑,对外发动反侵略战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和欧洲人真是截然不同。欧洲人成天只知道对外扩张。老想着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利玛窦也发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存在着致命的畸形。中国幅员如此辽阔,边界线如此悠远绵长。但他们缺乏认知和见识。对天朝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以至于,人人都认为,天朝上国,无奇不有。”
对于朝贡本质,当时有个意大利“中国通”利玛窦,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
利玛窦是个传教士,在中国前后逗留了28年,对中国国情可谓驾轻就熟。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利玛窦就强烈感受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论,“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正如他所指出:“中国人声称并且相信,中国的国土包罗整个的世界”。顾及素来秉持天圆地方说的中国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在献给明代皇帝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特意把中国置于世界中央,照顾了一下中国中心论的虚荣心。
在利玛窦看来,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导致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却如此彻底,以致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而对绝大多数外国,“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据他的观察,“与他们国家(指明帝国)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这些不值一顾的邻国,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占城等。
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
利玛窦在他的著述中写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外交官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中心论。利玛窦说:“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他说得一点不错,中国人“偶而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中国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他批评中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据利玛窦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国人“为了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在通用。”尽管过了4个世纪,“番鬼”这词至今仍在广东话中流行。
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如影相随的,就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惧与反感,以致“从不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正如《中国札记》所说,“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他们祖先的法制。”明朝这种誓死捍卫“祖先法制”的做法,不啻是当今某些鼓吹者的异代知音。
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利玛窦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华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拒绝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推动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中国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渐低落,利玛窦也成为中华帝国文明夕照的最后目击者之一。他在华长达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这里列举的,只是他对明朝人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的细微观察,已让400年后的国人有入木三分的感慨。
《中国札记》英译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尽头,但是无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这一论断,褒贬俱有。从贬的角度说,却让人如芒在背。难道在超阈度的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上,利玛窦所擿发的痼疾仍会旧病复发吗?但愿国人不要让这段话不幸而言中!
朝贡心理
纵观各朝史书记载,中国皇帝最得意最荣耀的一句话,大约就是“八方来贡,万国来朝”。即便是亡国之君,也喜欢在这方面大做文章。譬如隋朝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他在位时,“朝贡式贸易”搞得轰轰烈烈。每到大年正月,总要在都城大肆铺张。陪都洛阳大演百戏,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所有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的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
中世纪以后,虽然中国在政治文化上于世界渐渐失去影响力,但“朝贡”却一度发展到高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就迅即派出使者出使周边邻国,如:朝鲜,日本,占城,安南等国,通知诸国明继元统,宣扬大明国威。朝鲜,日本等国纷纷遣使进呈贺表以示臣服,一时间出现了“大明统一万方,天子文武圣神,以仁义礼乐君师亿兆,故凡华夏蛮貊,罔不尊亲。际天极地,举修职贡。自生民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的局面。
明成祖朱棣时,郑和七下西洋,出访国家遍布亚洲和非洲,中外交往盛极一时,大明国威“声闻四海”。据《明史》记载明朝时来华朝贡的国家多达150多个,中国式“宗主国—附庸国”体系在地理范围上达到了最大。但是,就像有人看穿隋炀帝“朝贡贸易”的本质一样,大明所谓“万国来朝”也都是中国皇帝“陪赔本赚吆喝”的面子工程,其实质是“假朝贡、真赔钱”。史书记载,隋炀帝免费招待“万国宾客”,这些费用一旦皇家结不了账,就要落在店家头上,这简直是皇帝拉着店家一起“赔本赚吆喝”。他死要面子让百姓活受罪,只为换得“名义上的尊重”而毫无实际利益,结果得不偿失。
利玛窦揭示中国式朝贡的本质,已经失去“宗主——藩属”的实质意义,那不是领导世界的组织,而是“夕阳国家”最大的面子工程。
然而,都知道中国皇帝“好面子”,不惜重金铸造外交“面子工程”,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在哪里呢?仅仅用“面子文化”能解释全面吗?
像朱棣这样的中国皇帝,并不像如杨广那般“智商”有恙,为什么也喜欢“假朝贡”、对外“倒贴”呢?他应该知道,外国对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为什么还是大把银子砸在外国人身上不心疼呢?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个人花谁的钱不疼?一是花别人的钱,二是花祖先的钱(中国民间有句谚语:崽花爷钱心不疼)。而这两种心态,中国皇帝全占。
中国虽是“家天下”,但国民在皇帝眼里,绝对不属于家庭成员,准确定位是“家蓄”,在皇帝眼里,与其说子民向皇帝纳税,不如说是他们向皇帝上贡。“取之于民”是真谛、“用之于民”是胡扯。至于“爱民如子”的说法,其含义与“鳄鱼的眼泪”差不多。
在“家天下”体制下,真正的“出活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上贡者乃是家蓄家奴,这才是中国君主的食物链下线,至于国外,大多是处在食物链上层的野兽,中国君主安敢寄望名副其实的朝贡呢?
从“夷狄”的角度设身处地想一想,“假朝贡”也在情理之中。这个一贯奉行“尚德抑武、不治夷狄、不干涉他国内政”大国,从未真正征服过我们、只是名义宗主国,我们何必诚惶诚恐“奉献”、真正纳贡呢?给足他们虚荣,换来我们的实际经济利益,你情我愿,一拍即合。
花别人的钱,交自己的友。出于这种心态,中国历代皇帝对于“假朝贡”乐此不疲。打肿脸充胖子,打肿的是“家畜”的脸,“光耀”的则是自己的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