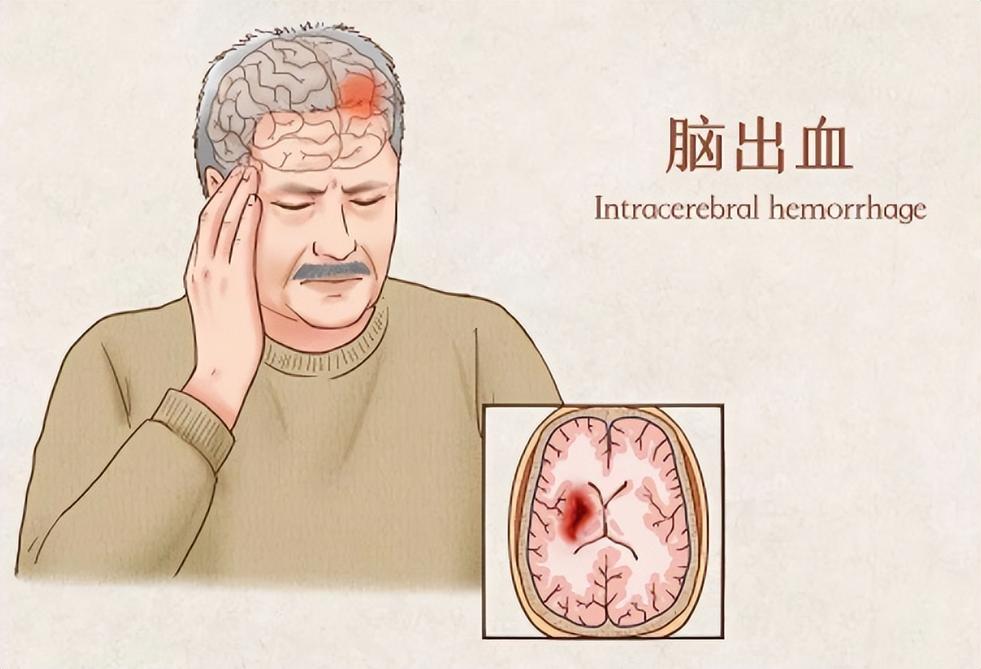通说
所谓侮辱是指利用小说作品公然谩骂、贬低他人人格,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诽谤是指利用小说作品捏造、传播虚假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我国首起被定罪的小说诽谤案是厦门作家唐敏的小说《太姥山妖氛》,社会影响最大的小说诽谤案是《荣誉的十字架》案。作家张士敏在塑造小说主人公于妙根时,采用了杨怀远许多独有的特征和事迹,同时又着力描写以杨怀远为原型的主人翁于妙根在“文革”中起来造反,完全失去了劳动模范的道德品质的高大形象,使人感到卑鄙丑恶。于的妻子因不满没有爱情的婚姻,与另一造反派头头通奸,后来投江自杀等情节。《荣誉的十字架》发表后,引起了“轰动效应”,看过小说并了解杨怀远先进事迹的人自然将二者联系起来,议论纷纷。杨怀远向法院起诉,法院立案后,上海有几十个知名作家联名向市领导写信,说鲁迅写《阿Q正传》,没有听说谁告鲁迅的。如果法院审理张士敏案,那么今后谁敢写作呢?航运机关、总工会、许多劳模则纷纷要求法院查清事实,还杨怀远清白。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被告人张士敏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之后又出现了湖北作家涂怀章小说《人殃》被控诽谤案;贵州遵义的历史小说《周西成演义》侵权案。小说侵权尽管有了司法定性的案例,但法律、文学界的争论 一直此起彼伏,未有定论,社会舆论也争议很大。
典型案例
案情简介:自诉人杨怀远诉称:1988年5月底,被告人张士敏在上海文学杂志《小说界》上发表了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小说的主人公于妙根与自诉人杨怀远的经历、身份、行为特征有一百余处相同,使读者将主人公夫妇视为两自诉人。被告人在小说中虚构了三个情节,对自诉人进行了恶毒的诽谤,使自诉人的精神受到创伤,人格受到侮辱,几乎酿成家破人亡。被告人的行为违背了宪法第三十八条。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追究被告人诽谤罪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张士敏辩称:《荣誉的十字架》是一部纯文艺小说。小说采用了杨怀远的一些素材,这在小说创作中是允许的。因为文学作品是源于生活的,虚构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自诉人的指控是不懂文学创作及其规律的表现,无法律根据,法院应驳回其起诉。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查明: 1985年春,被告人张士敏受工人出版社委托为自诉人杨怀远撰写传记。张士敏在对杨怀远采访过程中与杨发生矛盾,对杨产生怨恨,曾扬言要写小说“暴露”杨怀远以泄私愤。此后,张士敏撰写了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于1988年5月在上海文学杂志《小说界》第三期上 发表;1989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单行本。张士敏在塑造小说主人公于妙根时,采用了杨怀远许多独有的特征和事迹。如:杨怀远在旧社会讨饭时被狗咬伤腿,童年时当小工,解放后参军在部队当炊事兵;复员后到客轮当服务员,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用从部队带来的劳动工具 为旅客服务:“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批斗”,后被任命为上海海运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以后辞去领导职务,仍当客轮服务员;杨怀远用“母子板”、“百宝箱”、“方便桌”为旅客服务;服务工具“扁担”上被中外旅客刻满了签名和赞词;杨怀远1966年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与 著名劳动模范王进喜、孟泰、时传祥等在中南海睡地铺,周恩来总理深夜为他们掖被;1965年参加交通部组织的宣讲团到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港口作巡回宣讲;杨怀远获得的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等称号。张士敏还直接引用了“文化大革命”中杨怀远被批斗时在杨所住的船舱门口贴着的对联;杨怀远创作的《登天安门》和回忆旧社会苦难生活的诗歌;以及杨怀远与张士敏为写传记发生矛盾的基本情况等。这样使熟悉情况的读者看后,认为小说的主人公于妙根就是生活中的杨怀远。张士敏在小说中还虚构了三个情节加在主人公于妙根和其妻闵秀珍身上。一是于妙根在“文革”前巡回宣讲时,为了拔高自己,把解放前曾在一中农家做长工,说成在一地主家做长工,使该中农被戴上地主帽子,含冤受屈,家破人亡。“文革”后该中农找他算帐,使他无地自容。二是 于妙
根的妻子闵秀珍因不满没有爱情的婚姻,与造反派头头通奸。于妙根撞见后,为保住荣誉,宁愿蒙受耻辱,也不愿离婚,闵秀珍因此投江自杀。三是于妙根的儿子厌恶其父只要荣誉不顾一切的为人,决心与其父决裂,用自戕来推翻其父这座偶像。小说将主人公于妙根这个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客轮服务员描写成一个为了荣誉不顾一切而众叛亲离的人。张士敏供认,上述三个情节是他虚构的,用以达到影射杨怀远的目的。张士敏曾对替他誊写此小说稿件的人说:“我这部小说有些地方写的就是杨怀远,……我就是要惹惹他,让他跳出来。” 《荣誉的十字架》发表后,在社会上和境外引起了被告人所追求的“轰动效应”。一部分读者轻信小说内容,议论纷纷,给两自诉人精神上造成很大痛苦,工作和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两自诉人看过小说后,杨怀远手脚发抖,血压升高;余秀英嚎啕大哭,拿着“敌敌畏”要找张士敏还她的清白。杨、余的儿子原患忧郁症,看了小说后病情加重,曾经要自杀。法院在审理本案期间,明确告知张士敏:《荣誉的十字架》不得再版。但张士敏拒不接受,致使作家出版社于1989年2月出版了单行本,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张士敏先后共得稿酬人民币4358.72元。在庭审中,被告人张士敏承认他写《荣誉的十字架》有对自诉人出气的动机,引用了自诉人的大量素材,在客观上和事实上诽谤了自诉人,对自诉人造成了伤害,愿意赔偿损失,但认为《荣誉的十字架》是纯文学小说,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自诉人杨怀远、余秀英坚持认为张士敏犯了诽谤罪,应追究刑事责任。自诉人的代理人认为,被告人张士敏写的小说《荣誉的十字架》是指向两自诉人的,其主观上具有诽谤自诉人的直接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应予处罚。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张士敏写小说是创作行为,不构成犯罪。
审理及评析: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多次进行调解,因双方意见不一,调解未成。该院确认:被告人张士敏为泄愤报复,在塑造小说《荣誉的十字架》的主人公时,故意引用自诉人杨怀远独有的身世、经历、事迹、获得的荣誉称号、创作的诗歌等九个主要方面的特征,将主人公的基本特征写得与自诉人相同,同时虚构了损害自诉人人格和名誉的情节,对自诉人进行 诽谤,致使自诉人的人格受到了损害,名誉遭到了破坏。
在诉讼期间,被告人不顾法院的制止,使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出版单行本,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应予处罚。对自诉人由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被告人应予赔偿。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予追缴。鉴于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 认识,可酌情从轻处罚。该院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1991年2月27日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士敏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二、被告人张士敏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发表或出版小说《荣誉的十字架》。三、被告人张 士敏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358.72元予以追缴。四、被告人张士敏赔偿自诉人杨怀远、余秀英的经济损失计人民币1630.78元。宣判后,被告人张士敏没有提出上诉。
本案从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就受到社会上的很大关注。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某些虚构的事实,足以损害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诽谤必须是针对特定的人进行的,但不一定指名点姓,只要诽谤的内容足以表明被害人是谁,就可以构成诽谤罪。本案被告人张士敏因与自诉人杨怀远结怨,产生了以小说形式诽谤自诉人的直接故意。他在小说中并未指明杨怀远的姓名,但大量撷取杨怀远独有的身世、经历和特征加到小说主人公于妙根身上,足以使读者认定主人公于妙根就是生活中的杨怀远。
他在小说中虚构的三个情节足以损害自诉人的人格,破坏自诉人的声誉,对自诉人一家造成了严重损害。在涉讼后,他不顾法院的制止,使小说出版单行本发行,扩大了恶劣的影响,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张士敏的行为完全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士敏犯诽谤罪,是正确的。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既要保护公民的文学创作自由,又要保护公民的人格和名誉不受侵犯。张士敏写作和发表《荣誉的十字架》,是一般的小说创作还是以小说形式诽谤他人,必须从法律的角度上加以区别。(1)一般的小说创作,对模范人物的称许和批评都应是善意的,并无诽谤之心;而张士敏写《荣誉的十字架》是出于泄私愤图报复,有意诽谤自诉人。(2)一般的小说创作,为了塑造典型人物的需要,要求对生活中的原型进行典型化的艺术概括,以塑造出高于生活原型的新的文学形象,并且可以虚构一些合情合理的情节,以充分展现文学形象的本质特 征;而张士敏为了诽谤他人的需要,有意将属于自诉人独有的大量素材加到小说主人公身上,并且捏造三个违背情理的恶劣情节,以损害自诉人的人格和名誉。所以,张士敏写作和发表《荣誉的十字架》的行为,不是一般的小说创作,而是利用小说形式诽谤自诉人。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认真区别了一般的小说创作与利用小说形式实施诽谤的界限,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学术论文
《 试论“以小说”诽谤犯罪构成之成因》
撰写“虚构性小说”致人名誉受损,情节严重的,是否构成诽谤罪?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颇有争议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已有被认定犯罪的案例,但是争议并没有因此而解决。近年来随着小说涉讼日益增多,争议愈加突出,成为一个困扰法律界和文学界多年的难题。造成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诽谤罪构成要件和小说特征的不相容性,以致造成判断定性上的困难。如何认识撰写小说损人名誉行为的法律性质,对于正确界定“创作行为”和“诽谤行为”,保障我国宪法规定的“创作自由”和“人格尊严”两种权利的不受侵犯,正确实施刑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
撰写损人名誉的小说行为究竟是否构成犯罪?首先要考察小说能否成为诽谤罪的载体?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样式不可能成为诽谤罪的载体。理由是:按照刑法理论,诽谤罪构成要件之一,是诽谤行为必须针对特定的人进行。但是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样式,其塑造的人物形象虽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概括性、普遍性、不可能针对特定的人,简言之,就是小说这一形式不具有被利用进行诽谤的功能。
何谓小说?辞海中小说的定义是:“文学的一大类别,叙事性的文学体裁之一,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地描写,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小说的定义是从长期的小说创作实践中经过理论概括抽象而来。只要符合上述小说定义特征的,都可列入小说范畴。但是我们考察了上述小说定义可以发现这个定义并没有反映出小说特点和诽谤罪要件的不相容性。一些文学理论著作又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已经不是自然形态的社会生活,而是经过作家提炼、加工过的社会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已不再是生活中的某一个具体化的人了。按照这个说法,小说特点和诽谤罪要件的绝对不相容是很明显的。
作者认为:既不能一概而论断言小说不可能具有诽谤的功能,也不能不加分析地肯定讲小说具有诽谤的功能。我们只有在科学地、辩证地、深层次地分析小说的特点之后,才能拨开迷径,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
小说的特点其实蕴含有两层涵义。在这里我们把它分为形式特点和本质特点。形式特点是指小说可以虚构,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来反映生活。因此,只要形式上具备上述各要素,不管是自然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或者是意识流的作品,我们都可以称它为小说。那么这类仅具形式特点的小说是否具有诽谤功能呢?作者认为是具备的。因为这类小说通过写人叙事可以对生活中特定的人进行描写,或者诋毁,或者丑化。这里要指出的是,我们仅仅是说这类小说具有被用来进行诽谤的功能,并非说必然要被用来诽谤。但是小说除了具有形式上的一些共同特点外,有些小说还具备这样一些本质特点,这些特点是指:作家在创作小说时,运用形象思维,对生活素材进行一番提炼加工,经过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典型化过程,塑造出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典型形象。这样的典型人物形象,尽管有可能是以生活中的某一个模特为原型勾勒的,但两者之间不可能再具有同一性了。这类小说除了具有小说形式特点外,还同时具有文学创作应当进行形象思维的艺术特点,故根本不可能具有被用来进行诽谤的功能。我们考察小说能否成为诽谤罪的载体,不能统而言之,应从分析两种不同的小说特点着手来进行具体区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仅具备小说形式特点而不进行典型化创作的小说具有诽谤的功能,能够成为诽谤罪的载体,而两种特点都具备的小说不具有诽谤功能,不可能成为诽谤罪的载体。实践中,很多人都是从后一概念的层面上来谈论小说的,故认为小说不能成为诽谤罪的载体。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样式的成立,并不要求两种特点必须同时具备。有些小说不进行形象思维,不进行典型化创作,但是因为它具备了小说形式的特点,我们仍称之为“小说”。有些人用简单的三段论来推理,即小说是塑造典型人物的,不可能被用来进行诽谤,A是小说,所以A是不可能被用来进行诽谤的。这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没有错,结论似乎也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如果用辩证逻辑来分析一下大前提中的“小说是塑造典型人物的”,就可看出大前提有不真实的一面。因为并非所有小说都是塑造典型人物的。有些小说不塑造典型人物或者塑造时典型化程度不高,但我们仍称它们是小说。
小说特点和诽谤罪要件的不相容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诽谤罪构成的一个要件是诽谤内容必须是捏造和虚构的。而小说的一个特点恰恰是可以虚构,所以小说这一形式不能成为诽谤罪的载体。
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可以虚构。著名作家王蒙曾讲过:“小说最大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是‘假’的。没有假也没有小说。”从以上就诽谤罪的特点和小说的特点分析对照来看,诽谤罪是必须要虚假,而小说是禁止真实。这在它们各自的领域里都是绝对正确的,但它们之间却是不相容的。有些人就是以此为据,认为小说可以虚构的特点决定了小说这一形式不能作为诽谤罪的载体。作者认为对小说可以虚构这一特点应该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正像王蒙讲的没有假就没有小说,小说“假”的特点应从小说的全部内容上反映出来,只有当小说内容反映出整体假时才能认为是符合小说“假”的特点,也唯有如此,才是和诽谤罪的特点不相容。因为全部内容都是虚构的小说是不可能和现实生活完全吻合的,所以也不可能对生活中特定人进行伤害。小说禁止真实,对小说是虚构的这一特点应当准确理解为“小说是应当虚构的”。但是现在有些小说的内容是真真假假,鱼龙混杂;一部分内容是虚构,一部分内容是对生活的直接描摹。这种部分假的作品不符合小说是假的这一特点的全部涵义,违反小说禁止真实的原则。如果其部分“真”的内容是指向生活中特定个人的,那么和“部分真”并存的“部分假”就和诽谤罪要件中的必须捏造虚构就相容了。所以那些“真真假假”或者“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小说是能够成为诽谤罪的载体的。
(二)
以上我们只是就“小说能否成为诽谤罪的载体”这一命题对诽谤罪构成要件,结合小说特点进行孤立的单个的分析。要确认“以小说诽谤他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对诽谤罪构成之诸要件进行综合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诽谤罪的构成需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该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而且各要件之间应具有互相的因果联系。而由于“以小说进行诽谤”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在确认“以小说诽谤犯罪”时,应严格按照诽谤罪的构成要件来进行分析、判断定性。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判断。
1.作者是否具有诽谤的主观恶意。诽谤罪的构成,要求行为者有诽谤的直接故意。有些小说的作者,他们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艺术创作,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而是为了对特定的人泄愤报复,达到丑化、贬低他人名誉的目的。在作者的这种写作行为中,由于受作者诽谤主观恶意的驱使、支配,小说已经成为作者进行诽谤的手段、工具了。
2.具有诽谤内容的小说,完全背离创作小说应当进行形象思维,塑造典型形象,禁止“真实”的要求,对生活素材照抄照搬,仅进行一些形式上的重新编排、组合,描写故意真实化。作者之所以如此“创作”,并非作者的艺术功力差,创作水平低,而是作者在诽谤故意的驱使下,刻意地作如此安排选择,意图通过真实的描写,强烈暗示被诽谤对象,从而达到损人名誉的目的。
3.具有诽谤内容小说中的争议人物,必然直接指向生活中的特定人。要认定这种指向的成立,应具备两个条件。
(1)小说中争议人物的基本特征和生活中特定人的基本特征相同,但并非一定要指名道姓。姓名仅仅是人的外在符号,某个人之所以能和他人区别开来的客观标志,是某个人的基本特征(包括肖像特征、身份特征、经历特征、行为特征),而不是姓名。世界上同名同姓者很多,但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基本特征相同的人。构成个人在世界历史中的坐标点应该是行为特征,基本经历。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仅仅是个别特征相同不能确认是直接指向,同样的仅仅是个别特征不相同而基本特征相同的,也不影响直接指向的成立。同时,这种基本特征具有排他性,即生活中不可能再有第二人同时和这些基本特征相同。
(2)知情者读了小说后,均认为小说中的争议人物指向生活中特定的人。由于这类小说中的争议人物往往都不是指名道姓的,而仅从内容上来推知生活中特定人,故具有判断权的人应该仅限于熟悉、了解特定人基本特征的知情者。
以上两个条件之间具有一种互相依赖的紧密联系。因为只要两者的基本特征相同,知情人必然一眼就能看出;反之既然能一眼看出,两者之间的基本特征也必然相同。同时这两个条件的成立和作者的诽谤故意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作者之所以要将两者的基本特征写得相同,是为了达到诽谤的目的,否则作者即使有诽谤故意也无从去达到诽谤目的。
4.在小说虚构的内容中,有损害、贬低特定人名誉的具体描述。单纯的指向特定人并且有一些虚构的内容并不会损人名誉,当然更构不成诽谤罪。只有在作者虚构了足以损害特定人名誉的内容,才能产生损人名誉的结果。文学上的“虚构”和诽谤罪中的“捏造”在形式上虽然具有相同的一面,但两者在具体涵义、适用对象、适用目的上都有本质的区别。文学上的“虚构”是为了塑造典型的需要,作者之所以要“虚构”是为了艺术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而诽谤罪中的“捏造”是行为人进行诽谤的需要,是为了达到丑化、诋毁他人形象的目的。
5.小说是否被公开传播。诽谤的内容,只有经过在一定范围内的扩散、宣扬,才能起到损人名誉的作用。如果小说尚未发表,也从未被人传阅,就不能构成诽谤罪。
6.作者撰写损人名誉的小说行为情节是否严重。诽谤罪是轻罪,只有情节严重,才能构成诽谤罪。对以小说损人名誉的行为怎样认定情节严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
(1)从诽谤内容的恶毒中伤程度来看。贬低、丑化内容的性质、程度不同,名誉受损的程度也不同。分析诽谤内容的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以正确认定其诽谤情节的严重性。
(2)从被诽谤人的社会知名度来看。名誉和人身不可分离,人的社会知名度越高,一旦名誉受到损害,其损害程度也越高。所谓名誉是社会对人的价值评价,知名度越高的人,其价值评价的范围也越大。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进行诽谤和对一个社会著名人士进行诽谤,两者在名誉受损的程度、范围上是不一样的,这并非是对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律标准,所以要这样认定完全是由名誉的构成性质决定的。
(3)从小说传播范围的大小来看。传播范围大,知道诽谤内容的人多,被诽谤人受到的名誉损害也越大。诽谤内容随作品而存在,所以还要从作品出版的印数,重版的次数,发行范围的大小,实际流传的范围等来衡量、评定诽谤内容的传播范围。
(4)从小说发表后给被诽谤人造成的后果看。有些诽谤小说发表后,造成被诽谤人自杀,或者家庭生活的正常秩序被严重破坏等。但后果严重并不以自杀为唯一标志,故虽没有造成自杀后果,但只要其作品的诽谤内容足以使被诽谤人有自杀可能,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都应认定是后果严重。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5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司法实践中有人认为,在上述法条中的“其他方法”并未规定小说可以被用来作诽谤的工具。法无明文不为罪,所以在文艺尚没有立法的情况下,根据现有法律条款的规定小说这一形式不应确认为诽谤工具。
作者认为所谓“法无明文不为罪”是指某种行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有罪的,不认为有罪。在这里,有些人将“行为”和“方法”这两个在刑法上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刑法惩罚的是“有罪的行为”,而不是“犯罪方法”。在以小说诽谤犯罪中,根据我国刑法主要是考察作者在小说中有无对特定人的诽谤行为,而不在于他用什么方法。方法为行为服务,不同的方法可以服务于同一行为,方法的不同不影响诽谤行为性质的确立。刑法是以行为定罪,而不是以“方法”定罪。同是杀人,用刀杀人是杀人行为,用毒药毒死人也是杀人行为,尽管杀人者采用的方法不同,但不改变杀人行为的性质。所以小说作为一种方法在诽谤罪构成中具有值得研究意义的,仅限于“小说是否具有被利用进行诽谤的功能”这一命题上。
作者认为我国刑法145条中规定的“其他方法”,其涵义理应包括小说这一形式。这里的“其他方法”,是一个开放性的规范。因为诽谤的方法、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在法条列举中不可能去穷尽所有的方法,所以在立法上就采用概括的表述方式,以适应复杂的司法实践。我们考察任何一种方法,只要其具有诽谤功能,能达到损人名誉的目的,都可以被包括在“其他方法”中。在145条中现在只列举了“大字报”、“小字报”,但在实践中有人用绘画来进行诽谤而被定罪,那么能否因为法条中没有明文规定绘画这一方法而应认为这种行为不构成诽谤罪呢?显然不能。在世界各国刑法中对诽谤罪的方法表述在立法上一般都采用开放性的规范。例如美国纽约州刑法第1340条规定。“怀有恶意出版文字印刷品、图片、画像、标记或其他非口头形式的物品,使活着的人,或对去世的人的追忆,受到憎恨、藐视、嘲笑或指责,使他受到孤立或有受到孤立的倾向,或使他人或任何公司、社团,在经营或职业上的声誉有受到损害倾向的,皆为诽谤。”在上述法条中,虽然也详尽列举了“文字印刷品、图片、画像”等方式,但由于方式的列举不可穷尽,故在最后又作了开放性的规定“或其他非口头形式的物品”。再如日本刑法第309条规定:“公然摘示事实,侵害他人之名誉者,不管其事实是否真实,处五年以下惩役或禁锢或三十万以下之罚金。”在这个法条中,根本不列举任何诽谤方式,只要符合上述法条规定的要件,任何方式只要其具有诽谤功能,都可以定罪。遍览世界各国刑法,现在还没有任何国家的刑法因为“小说”的特殊性而明确规定应当将“小说”排除在诽谤方法之外的。相反的,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利用“小说”诽谤他人被定罪或课以罚金的案例。由此可见,中外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未将“小说”排斥在诽谤方法之外。
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人认为,要对写小说损人名誉的行为是否构成诽谤罪作出法律判断,应当在文艺立法之后。作者认为,在文艺立法中能作出明确规定固然是好,但在目前文艺尚没有立法的情况下,也根本不影响我们根据刑法的现有规定对以“小说”诽谤他人的行为作出是否有罪的判断。要确认某种行为是否有罪,确认的基本标准只能是我国的基本法——刑法。今后即使文艺立了法,但在非刑事法律规范中作出的刑事规范,也是对现有刑事法律的补充、解释、完善,但不能改变刑事法律规定,或者和这些刑事法律规定相抵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对“利用小说进行诽谤”的行为进行审判,实质是对文学原理的审判。这种看法完全曲解了刑法理论,混淆了是非。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犯罪”是一种孤立的个人对统治关系的反抗行为。犯罪是一种人的行为,撇开人的因素,孤立地讨论小说能否被用来犯罪毫无意义。法院要审理的是行为人在写作小说中有无诽谤行为,这种诽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不是撇开人的行为去审理小说本身,更不是审判文学原理。“小说”在案件中的意义仅仅是它是否被利用成了诽谤的工具。如根据上述观点推而论之,如果有人利用漫画进行诽谤,那么法院审理的又是“漫画艺术”本身了,由此可见这种看法的荒谬性。
对“以小说”进行诽谤,情节严重的,是否构成诽谤罪进行判断,作者认为正确的判断方法应该是:应当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诽谤罪的严格规定,对涉讼的小说及作者按照诽谤罪构成之诸要件,结合小说形式的特殊性,进行科学的、综合的、辩证的分析判断,最后来确定作者的行为究竟是“创作行为”还是“诽谤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刑事处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保证作者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又能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